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
甲骨文

- 中国历史故事-小虎历史故事网
- 2023-08-05 07:00
- 小虎历史故事网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首發)
許子瀟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先秦時期的顱骨刻辭,屬商周甲骨文範疇,因其質料的特殊性,歷來受學界重視。從以往學界的研究成果來看,顱骨刻辭與商周社會的祭祀、征戰、巫術、喪葬等問題密切相關。但是目前學界在這些刻辭的斷代、用途等問題上尚未取得共識,在遞藏和著錄信息上也有可以商榷之處。本文擬在整理每片刻辭情況的基礎上,結合前人研究,對以上問題提出管見。
現存商周顱骨刻辭共15片,含商代晚期14片,西周早期1片,按照現藏處分述於下:
一、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1.……丑,用于……義友[1] 《合》38762
本片由胡厚宣辨認出。1945年抗戰結束後,胡先生在各地搜求甲骨材料,于北京慶雲堂碑帖鋪購得此片,[2]並著錄在《京津》5282號。
胡先生在慶雲堂共得甲骨四百餘片,這批甲骨的來歷不明,唯其中有一片四方風刻辭可以和“中研院”第十三次發掘所獲的半塊甲骨相綴合,可惜如此孱弱的線索並不能指明本片顱骨刻辭的來源。[3]胡先生判斷此片時代在第四期(案,胡先生所言的第四期,即帝乙帝辛時期,下文同),[4]這是合理的,從字體來看本片確屬黃類。
這片刻辭的去向依胡先生自述乃歸北京圖書館,然而郭若愚提到他50年代去北圖參觀時並未見原物,並猜測“大概不知被分售到哪裡去了”。[5]現知此片實存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是胡先生所贈,董作賓和張秉權都曾目驗實物,[6]當可信。
關於本片刻辭的行款,董作賓曾有論述,認為是下行而左,這是正確的。[7]骨片右側邊緣,即人體顱骨的矢狀縫。我們認為,在契刻時,這條腦中部的骨縫所起到的作用很可能類似卜甲的中縫或卜骨的臼邊,是其兩側刻辭行款的對照線。[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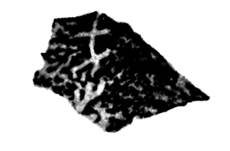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2.……武…… 《甲》3739
本片是唯一一片科學發掘所得的商代刻辭顱骨,現藏臺北史語所,最先著錄在《甲》3739號。此片刻辭出土時,學者們並未辨認出它是一片顱骨,所以僅當作一般的龜甲著錄,這個失誤在屈萬里的《殷虛文字甲編考釋》中得以糾正。[9]需要指明的是,宋鎮豪[10]和王宇信[11]等人都認為此片即《合》27741,不確。《合》27741實為《安明》2129,為明義士舊藏,現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本片是1933年12月14日殷墟第八次發掘所獲,出土坑位為D100,層位為深度為0.35米的地面層下。石璋如認為此片屬一期,[12
中国历史笑里藏刀的故事
]李學勤指出“武”字乃商末寫法,系商王名號之殘。[13]檢D100位於D區中部偏東,夾在甲三、甲四與甲十一基址之間,杜金鵬認為此片出土於甲十一基址的夯土層中,[14]非是。D100只是一個基旁窖,與相鄰的三個基址之間的從屬關係並不清楚。第八次發掘的灰坑8H:11、8:H12壓在甲十一基址下,朱鳳瀚指出兩坑所獲甲骨多屬於賓組一B類,所以甲十一基址的始建年代當不早于武丁晚期。[15]實際上不僅甲十一基址,甲組建築基址多為武丁中晚期始建,第八次發掘的D區所獲甲骨,也以一期為多數,較少見到後期材料。這些線索似乎暗示我們不宜將此片顱骨刻辭的時代定的過晚。但是從問題的另一個方面來看卻不是這樣。甲組基址雖然始建年代偏早,但作為寢宮一直沿用至殷墟晚期,[16]這片區域完全有可能出土乙辛時期的遺物。D100及附近諸坑沒有相應的伴出甲骨,D100坑中此片為一“孤例”。況且顱骨刻辭材料具有一定特殊性,對於它的斷代研究,未必要受D區其他甲骨斷代成果的制約。刻辭中的“武”字是唯一明確斷代線索,其書體確為黃類風格,綜合考慮,我們仍以李學勤說是。
二、國家圖書館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3.方伯[用]……《合》38759
本片首次著錄在《京津》5281號,胡厚宣所據為劉體智藏拓片,原骨為劉體智所有。胡先生並未交代此拓片的來源,我們可以據其他信息略作推測:
1947年,胡先生在復旦大學任教,常去市區拜訪劉體智,參觀其藏品,還曾將劉先生的十八卷拓本集《書契叢編》借回研究。劉氏藏骨雖豐,但顱骨刻辭十分扎眼,胡先生可能就在這時得到了此片拓本。[17]然與《寧滬》不同,《京津》一書中著錄的多為胡氏在北京、天津兩地所獲材料,他把上海獲得的本片編入,可能是想與書中5282號顱骨刻辭合觀。不過這裡還有另一種可能,《京津》中有在北京隆福寺粹雅堂購買的劉體智藏骨拓本,此片很可能混入其中。[18]實際上,據趙愛學統計,《京津》中劉體智的舊藏達1800片左右,數量可觀。[19]建國後,此片刻辭隨劉體智的其他甲骨被文化部收購,經社科院考古所制拓後調撥國圖保存。陳夢家當時參與了這項工作,這也是《殷虛卜辭綜述》中曾著錄此片刻辭照片的原因。[20]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圖 1 《綜述》附《合》38759照片
經鑒定,此片為右頂骨前內角之一塊。[21]胡厚宣斷代為四期(帝乙帝辛),可從。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4.……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本片照片著錄於《綜述》圖版十四·上,亦為劉體智舊藏,1953年考古所傳拓時發現,後調撥國圖。從陳夢家著錄的照片來看,骨片背面無鑽鑿。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圖 2 《綜述》附《合》38761照片
本片的時代當為第五期,辭中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三、故宮博物院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5.[白](伯)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這片拓本最早公佈在胡厚宣《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下篇》,[23]胡先生言此片另見其著《甲骨續存補編》9067號,今核原書並無9067號甲骨。曾毅公《甲骨文捃》中此片編號為304,可知原骨為凡將齋馬衡舊藏。[24]1952年,馬衡將所藏甲骨捐給故宮博物院。2017年3月,故宮在延禧宮舉辦“大隱於朝——故宮博物院藏品三年清理核對成果展”,在甲骨單元展出本片,但是展覽說明中提到此片為1974年文物局交撥的明義士舊藏,不確。
本片時代胡厚宣定為武丁時期,李學勤定為商末。李先生認為本辭中的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合》20989 師組
《合》6081 賓組
《合》24356 出組
《合》36518 黃組
其“口”上均從“一”作為指示符,表示說話時口向外的動作,不可省略。故此字仍以釋“白”為宜,讀為伯。
過去學界多認為伯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6.……尸(夷)方[白]伯……祖乙伐 《合》38758
本片原骨為明義士舊藏,摹本最早由明義士著錄在1933年的《齊大季刊》第二卷第二期,[28]《合集》所收拓本中“尸”字已經基本殘去,故明氏摹本殊為重要。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圖 3 《合》38758明義士摹本
李學勤認為此片現存臺北史語所,這是不正確的。[29]據學界整理可知,明氏生前所有的甲骨藏品現存六處,為故宮博物院、山東省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加拿大維多利亞藝術館以及英國漢普夏孟克廉夫婦私藏。[30]這六批材料的遞藏經過、數目都很清楚,明氏藏骨沒有理由也沒有機會流入臺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胡厚宣為編纂《甲骨文
中国历史故事我的感想
合集》曾在全國範圍內調查、拓印甲骨,胡先生去世後,後人將其工作成果整理為《甲骨李清照中国历史故事
續存補編》出版,《續補》卷一中“故宮藏甲骨選片”的1.26.1號正是本片,可以說明此片目前確藏故宮。本片時代李學勤認為屬商末,可從。[31]
四、社科院歷史所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7.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本片最早著錄于胡厚宣《續存》1.2358,現藏社科院歷史所。原藏、時代均不可考。
五、上海市博物館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8.[隹]…… 《合》38764
此片拓本最早著錄於《掇二》87,時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現藏上博。時代不明。
六、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9.……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此片為河井仙郎(荃廬)舊藏兩片顱骨刻辭之一,《合集》未收,照片著錄在1983年松丸道雄編著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拓片見荒木日呂子《東京國立博物館保管的甲骨片》一文。[32]骨片背面無鑽鑿,但有偽刻若干字。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圖 4 《东京》972照片
七、東京國立博物館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10.……丰沚……五[丰]…… 《日蒐》2.180
此片為小倉武之助舊藏,首次著錄在1959年松丸道雄編著的《日蒐》中,照片見荒木日呂子《東京國立博物館保管的甲骨片》。背面無鑽鑿。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圖 5 《日蒐》2.180照片
辭中丰字下部填實,屬黃類風格,可釋為封。卜辭中的“丰”前常加數詞使用,辭例作“X丰”、“X丰伯”、“X丰方”等。荒木女士提到“丰”字指方國,這是合理的。但是她認為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八、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11.大甲 《懷》1914
據李棪介紹,這是一片男性人頭枕骨,原藏英國葉慈處,20世紀50年代轉讓給李先生。[34]本片1966年曾在香港展出。至於後來是如何到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不可考。刻辭時代亦不明。
九、情況不明或被毀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12.……用 《綜述》圖版十三中
本片的照片和拓本是陳夢家自藏,另收其未刊拓本集《甲室雜集》和《解放後甲骨的新資料和整理研究》一文中,[35]來源和遞藏情況均不清楚。從照片來看,骨片背面無鑽鑿。僅存一“用”字,無法斷代。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13.王君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本片為1984年長安灃西張家坡西周墓地M157所出,是下頜骨的一部分。張政烺將刻辭釋為“王君穴”,認為和擇穴下葬有關,古人選定墓穴之後會用人骨作為標誌。張長壽從之。[36]
我們認為,M157是井叔家族墓地中規制等級較高的一座,墓主的身份根據簡報意見當為一代井叔。[37]“王君穴”三字若理解為“君王下葬所選定之墓穴”,那麼與墓主的身份是無法對應的。辭中最後一字釋“穴”也很可疑。[38]這片刻辭的材料性質與內容都十分特殊,有待進一步研究。M157的時代依發掘簡報定為西周懿孝時期,這也是本片的年代下限。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14.……盧……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本片為河井仙郎(荃廬)舊藏兩片顱骨刻辭之二,在二戰期間毀於戰火。[39]最早著錄為林泰輔1921年的《龜甲獸骨文字》2.26.5號。1935年的《殷契遺珠》著錄為298號,亦即《合集》所本。不同拓本之間的差異對於刻辭釋讀有較大影響,有必要詳細說明。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圖 6 《珠》298
圖 7 《龜》2.26.5
以往的釋文,都將左側字釋為“戔”,[40]這可能是受到了《珠》與《合集》拓本的誤導。在《珠》和《合集》的拓片中,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而《龜》2.26.5拓本就沒有這樣的情況,所從人旁十分明晰,右旁當從裘錫圭所釋“柲”字初文,[42]並非“戔”字。盧字在卜辭中有“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电影英文介绍中国历史故事
品時,常用“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本片的時代可依據字體卡定。辭中的“盧”字,集中出現於早期組類中,無名組以後就很少見了。[44]目前可以確定的時代最晚的“盧”字見《合》28095,本片屬於馬智忠分類中的無二B類,時代主要在康丁一世,上不到廩辛,下不過武乙前期。[45]也就是說,“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15.……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本片為焦智勤近年新發現的刻辭顱骨。《殷墟甲骨拾遺》著錄拓片與摹本,將釋文定為“……□……武乙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以上即為目前已知的所有顱骨刻辭,需要說明的是宋鎮豪和王宇信[48]都認為《合》3435為一片刻辭顱骨,此片為劉體智舊藏,現存國圖,細審之當為一般的師賓間類卜甲。這是需要更正的。下面簡單討論商代刻辭顱骨的史料價值及史學意義。
辨認出顱骨刻辭只是第一步,對它們進行較為深入的討論,實際上始自陳夢家。[49]經過幾代學者的研究,現在學界大都認為顱骨刻辭是一種記事刻辭而非卜辭,持這種看法的主要有陳夢家、[50]王宇信、[51]宋鎮豪、[52]黃天樹、[53]李學勤[54]等人。而作為刻辭載體的顱骨,學界一般認為是一種祭祀貢品,陳夢家、于省吾、[55]胡厚宣、[56]宋鎮豪等人主之。不過,同樣是記事刻辭,刻寫的目的卻有不同,胡厚宣、陳偉湛[57]認為顱骨的刻辭的目的是為了銘功炫耀,而不是為了記錄祭祀的對象等信息。另一方面,陳夢家、王宇信等人雖然承認顱骨是一種特殊的祭品,但是在引證文獻時,他們都使用了《史記》、《戰國策》中以人頭骨作為飲器的記載,[58]這就讓我們對這些顱骨究竟是祭品還是實用器產生了疑問。
我們對顱骨刻辭的認識如下:
首先,從多片刻辭的內容來看,這些顱骨乃祭祀祖先所用之物,應當是沒有疑問的,我們承認“祭品說”。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用作祭品的顱骨,未必不能用來占卜,其上的刻辭亦存在是卜辭的可能。從《合》38761、《東京》972、《日蒐》2.180等片的背部照片來看,這些骨片未經鑽鑿,這種情況和肋骨刻辭十分類似。肋骨刻辭在發現之初,學者們也認為其上所刻並非卜辭,[59]然而經過李學勤等人的研究,我們已經可以肯定當時存在一些不為現代人知的冷卜法,肋骨卜就是其中一種。[60]實際上,在人類學材料中,也有用顱骨占卜的例子。[61]所以,以往學界認為它們不是卜辭而是記事刻辭的觀點只能說是一種“合乎情理”的猜測,證據並不充分。
其次,《合補》11099的“伯

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
再次,由我們對於每片刻辭時代的大致介紹可知,顱骨刻辭在殷墟早晚期都存在,並不如李學勤所言都集中在五期。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大部分刻辭顱骨還是屬於五期的。《合》38758、《合》38761、《日蒐》2.180等片中的線索似乎都指向了乙辛時期商王朝的幾場對外戰爭。如果這些顱骨真的屬於敵方首腦,那麼它們很可能包含了一些殷人在戰爭過程中集中獲得的材料。
最後,刻辭顱骨可能與當時存在的“毀器”習俗有關。殷墟發現的甲骨,因材料本身的性質,埋藏之後容易破碎。即便如此,我們依舊發現了為數不少的整版大龜大骨,這說明殷墟的龜甲和胛骨在埋藏時候,大部分應該是完整的。顱骨與一般的甲骨不同,其本身近球體,所以在埋藏時候就可以很好地分散土壤帶來的壓力,在小屯宮殿區的夯土基址內以及殷墟多座墓葬、祭祀坑中發現的顱骨,都是基本保存完好的,沒有像刻辭顱骨碎裂程度如此嚴重的情況。[62]這種現象提示我們刻辭顱骨在使用過後,應該是經過了人為的銷毀之後才廢棄的,在某種程度上也算一種“毀器”行為。關於古代毀器行為的人類學含義,有多位學者進行過專門研究,可以參看。[63]比照其他毀器的情況,我們認為將刻辭顱骨打碎的目的,可能是為了更好地發揮顱骨的巫術效力,將祭品奉獻給祖先。
補記:
小文初稿于2019年5月17日寫定。近日方稚松先生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九輯)》發表文章《殷墟人頭骨刻辭再研究》,我們在撰寫時尚未拜讀。方先生文與拙文在使用材料以及結論等方面有不少相合之處,讀者可自行比較。
本文所引甲骨著錄簡稱表:
《京津》《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
《掇二》《殷契拾掇二編》
《甲》《殷虛文字甲編》
《合》《甲骨文合集》
《安明》《明義士收藏甲骨文字》
《續存》《甲骨續存》
《續補》《甲骨續存補編》
《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圖版篇》
《日蒐》《日本散見甲骨文字蒐匯》
《懷》《懷特氏收藏甲骨文集》
《珠》《殷契遺珠》
《龜》《龜甲獸骨文字》
[1]釋文採用寬式,後文同。
[2]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北京:商務印書館,1951年3月,第47-48頁。
[3] 同上注。
[4] 胡厚宣,《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序》,上海:群聯出版社,1954年3月,第1頁。
[5] 郭若愚,《殷契拾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6月,第112頁。
[6] 董作賓,《殷代“文例”分“常例”、“特例”二種說》,載《中國文字》第六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2年1月;張秉權,《甲骨文與甲骨學》,臺北:國立編譯館,1988年9月,第196頁。
[7] 參上注董氏文。
[8] 相關研究參看黃天樹,《甲骨拼合集·附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8月,第501-538頁。另外,同樣的情況亦見《甲》3940、3941兩片鹿頭刻辭。
[9] 屈萬里,《殷虛文字甲編考釋》,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年6月,第786頁。
[10] 宋鎮豪,《中國風俗通史·夏商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1月,第734頁。
[11] 王宇信、揚升南,《甲骨學一百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9月,第249頁。
[12] 石璋如,《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丁編·甲骨坑層之一-一次至九次出土甲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年,第175頁。
[13] 李學勤,《殷墟人頭骨刻辭研究》,收入《海上論叢》(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第6-7頁。
[14] 杜金鵬,《殷墟宮殿區建築基址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年11月,第88頁。
[15] 朱鳳瀚,《論小屯東北地諸建築基址的始建年代及其與基址範圍內出土甲骨的關係》,《古代文明》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16] 參注14,第94頁。
[17] 胡厚宣,《關於劉體智、羅振玉、明義士三家舊藏甲骨現狀的說明》,《殷都學刊》,1985年第1期,第2頁。
[18]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北京:商務印書館,1951年3月,第50頁。
[19] 趙愛學,《國家圖書館的善齋舊藏甲骨及其著錄》,《文津學志》,2017年,第372頁。
[20]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月,圖版十三·上。
[21] 陳夢家,《解放後甲骨的新資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5期,第5頁。
[22] 王子楊,《揭示帝乙、帝辛時期對西土的一次用兵》,《甲骨文與殷商史》新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第227-228頁。
[23] 胡厚宣,《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文物》,1947年第8期。
[24] 郜麗梅,《<甲骨文捃>的初步復原》,《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第94頁。
[25] 見注13,第4-5頁。
[26] 張惟捷,《晚商人物“師般”史跡考述-並論文獻中“甘盤”的相關問題》,《甲骨文與殷商史》新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83-184頁。
[27] 見上注。
[28] 明義士(加),《表校新舊版<殷虛書契前編>並記所得之新材料》,《齊大季刊》,1933年2期。
[29] 注13,第2頁。
[30] 方輝,《明義士和他的藏品》,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65-193頁;
董林夫,《CrossCulture and Faith_ The Life and Work of James Mellon Menzies》,多倫多:多倫多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22-138頁;
李學勤、齊文心、艾蘭,《英國所藏甲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9月,第4頁。
[31] 見注13。
[32] 荒木日呂子,《東京國立博物館保管的甲骨片-有關人頭骨刻字的考察》,《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第69頁。
[33] 孫亞冰、林歡,《商代的地理與方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64頁。
[34] 李棪,《殷墟斫頭坑骷髏與人頭骨刻辭》,《中國語文研究》,1986年第8期。
[35] 見注21。
[36] 張長壽,《說“王君穴”》,《文物》,1991年第12期。
[3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隊,《長安張家坡西周井叔墓發掘簡報》,《考古》,1986年第1期,第27頁。
[38] 許子瀟,《西周甲骨材料整理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第68-69頁。
[39] 松丸道雄[著]、宋鎮豪[譯],《日本收藏的殷墟出土甲骨》,《人文雜誌》1988年第9期。
[40] 見注10、注11。
[41]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12月,第21-32頁。
[42] 裘錫圭,《釋“柲”》,《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1頁。
[43] 字形截取自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639/821頁。
[44] 劉釗等,《新甲骨文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300-311頁
[45] 馬智忠,《殷墟無名類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6月,第143、442頁。
[46] 見注41,第52頁。
[47] 何景成,《試釋甲骨文中讀為“廟”的“勺”字》,《文史》,2015年第1期。
[48] 見注10、注11。
[49] 見注20,第326-327頁。
[50] 見注20。
[51] 見注11。
[52] 見注10。
[53] 黃天樹,《甲骨文中有關獵首風俗的記載》,《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夏之卷,第23-30頁。
[54] 見注13。
[55] 于省吾,《從甲骨文看商代社會形制》,《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報》,1957年第2期第3期合刊,第111-112頁。
[56] 見注23。
[57] 陳偉湛,《甲骨文簡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第92頁。
[58] 見《史記·大宛列傳》、《戰國策·趙策》。
[59] 見注20,第6頁。
[60] 李學勤,《鄭州二里崗字骨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4頁。
湯銘,《試探牛肋骨刻辭的貞卜意義》,《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76-185頁。
[61] 伊里安島的厄剌伯和莫累島的土著民族認為,他們之所砍下死者的頭顱,主要是用於占卜吉凶。見劉黎明,《刑天神話·獵首習俗·頭骨崇拜》,《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第85頁。
[62] 如《甲》3739出土坑位旁的甲十一基址夯土中就出土了比較完整的顱骨。見石璋如,《中國考古報告集·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乙編·殷虛建築遺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年,第20-53頁。乙七基址的M80、M81、M85,西北崗王陵區的墓葬及祭祀坑,都有被砍下的顱骨作為殉葬品的現象,例證非常多,不繁引,這些顱骨大多保存完整。
[63] 何崝,《商代卜辭中所見之碎物祭》,《中國文化》第十一期,1995年,第81-83頁。
郜向平,《商墓中的毀器習俗與明器化現象》,《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1期,第44-45頁。
点击下载附件: 2037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docx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912/06/858051.html
以上是关于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甲骨文-許子瀟:商周時期顱骨刻辭材料整理;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15344.html。
上一篇:吕氏春秋-《吕氏春秋》题旨新解
猜你喜欢
- 历史-武丁把妇好杀了?史料记载并不是这样的 2023-08-14
- 中国历史-妇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史记载的女将军 2023-10-17
- 甲骨文-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文字 商代甲骨文的介绍 2023-10-14
- 历史-总以为她是神话人物 没想到发现了她的墓葬! 2023-10-12
- 历史-妇好是怎么死的?揭秘妇好的死亡真相? 2023-10-12
- 夏朝文字-夏朝有文字吗?中国古代夏朝的文字存在证据 2023-10-12
- 夏王桀-美人计加苦肉计 一男一女两人如何颠覆夏朝? 2023-10-11
- 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史记载的女将军是谁 2023-10-10
- 商高宗-武丁妻子:一生四嫁能征惯战的奇女子妇好 2023-10-10
- 中国古代史-我国古代史上五位著名女将 居然没有花木兰 2023-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