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近代历史进程思想巨匠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
-
影响,近代,历史,进程,思想,巨匠,徐继畲,及其,

- 中国历史故事-小虎历史故事网
- 2023-08-11 22:42
- 小虎历史故事网
影响近代历史进程思想巨匠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影响近代历史进程思想巨匠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影响近代历史进程思想巨匠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

影响近代历史进程思想巨匠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
影响近代历史进程思想巨匠徐继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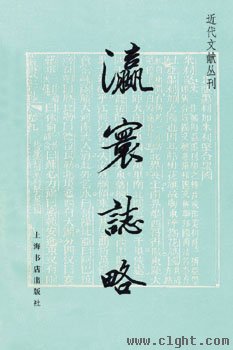
影响近代历史进程思想巨匠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
《瀛环志略》
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东冶人。幼年随父寓京,师从高鹗。父徐润第,进士出身,有《敦艮斋遗书》传世。徐继畲亦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屡屡升迁,官至福建巡抚。
与林则徐冲突
徐继畲任福建巡抚期间,与在家养病的林则徐发生冲突。
冲突起因,是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一名英国籍传教士和一名教会医生,租赁福州城内神光寺房屋,得到侯官县县令兴廉批准。
徐继畲得知后,立即申斥兴廉,令其劝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执尔却以此事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为借口拖延。
林则徐一听说,马上就发难,要他将传教士赶走。可他认为,这是件小事,由一时疏忽造成,没有必要大动干戈,最好设法让他们自己离去。
而林却突然发作起来,忽儿出绅士公启,以示驱逐;忽儿又写生童告白,遍城粘贴;还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准备动武。但徐和总督刘韵珂都觉得这样慌里慌张准备打仗,是召敌来攻,大为失计,因此,不肯附和林的倡议。
林怒而投信京中,鼓动群僚来攻。攻之者,有一学士、两御史。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先参他抚谕无方,继而参他袒护属员、包庇汉奸。
在林则徐看来,对于来犯之夷,要么剿,要么抚,要么剿抚并用,这是原则,是华
用词概括中国历史故事的特点
夷之辨,而徐继畲,既不剿,也不抚,连华夷之辨都不讲了!徐继畲想干什么?要对英夷无为而治?不是!那是搞外交。
什么是外交?天下观(见附注)里无外交。不是主权国家,就不知何谓外交。走出天下观,走出华夷之辨,就会在剿与抚以外,发现还有个外交的空间。
近代以来,最早意识到在天下观之外还有外交的,是徐继畲。
神光寺事件,在林则徐看来,还是天下观内“剿”与“抚”两条路线的斗争,“剿”是爱国,“抚”是卖国,连“剿抚并用”的中间路线都没有。因为英夷和传统蛮夷不同,对付蛮夷,可以弱则剿、强则抚,用天下观牢笼得住。
而英夷自有一套,他们要天朝放弃天下观,进入他们那一套去,用他们那一套来约束天朝,使天朝降格,降到与夷同等规格上去。
林则徐站在天朝的立场上,坚决反对“他们那一套”,对“他们那一套”了解越多就越反对,因为他发现,“他们那一套”与天朝格格不入,在“他们那一套”里,根本就没有天朝的立足之地,天朝只能委曲求全,自居于夷。
因此,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者中间没有调和余地。天朝起东风,英夷刮西风。东风吹,战鼓擂,那是天朝爱国主义。
徐继畲不搞“东风吹,战鼓擂”那一套,并非图省事,或怕事。第一次鸦片战争,英舰北上,攻破厦门,那时,他任汀漳龙道道台,驻地漳州,与厦门仅一水之隔。他像林则徐一样,积极备战,但引而不发,以静制动。英人见他有备,便转攻宁波,而他则因守土尽责,备战有方,升迁至福建巡抚。
据《徐松龛年谱》记载,他在备战期间,曾经问过夫人:城破了,我就战死,你怎么办?夫人笑着说:那就一起死吧,这还用商量吗?!
但这次神光寺事件,他认为林则徐是小题大做了。区区小事,完全可用外交手段解决,英人一拖二赖不肯走,他就阳奉阴违与其磨。由他管辖,办法有的是,他要让英人自动离去。
读近代史,有一句老话,叫做“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这话应该改一下:落后会吃亏,但不一定挨打;落后,还要做老大,那就一定要挨打。
日本也落后,但日本没有挨打,因为日本没有做老大。大清是天朝,天朝是天下的老大,是中世纪老大,新兴资本主义,专打中世纪老大。
只有以老大自居,才会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将洋人赶出城去。
日本人不做老大,让洋人住在城里。洋人与日本人居住在一起,就要遵守日本法律,就谈不上什么“治外法权”,也不会出现所谓“租界地”。
可在老大的天下里,这些玩意儿都出现了,有了“治外法权”,夷就没治;有了“租界地”,如花似锦的一统江山— —大清皇舆,就被撕裂了口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老大挨打了,被打出“治外法权”,打出“租界地”。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虽然也有老大心理,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永不屈服,将文明的抗争进行到底,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高扬了中华理想主义。
怕挨打吗?不怕!将挨打进行到底,最终就会取得胜利。打败了,要割地,要赔款,要亡国,怕不怕?不怕!永不言败,胜利就在自己手里。
他和文天祥似一样,是一种伟大的文化才能产生的伟大人物。值得他用生命去捍卫的文化,必定有其崇高价值,他愿为之而生,为之而死。
就此而言,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和勇气。但他没有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和新世界正在来临,一种新的文化就要诞生,而徐继畲得风气先。
林与徐的分歧在于,一个在为旧文化抗争,一个在为新文化欢呼。这样难以察觉的分歧,决定了他们在神光寺事件上的态度——容忍和愤怒。
徐是容忍的,侯官县令看似一时失误,实乃他平时影响所致。他本人就常与洋人来往,所以他的下属,也往往放松了 “夷夏之防”这根弦。
可侯官是林则徐的老家,稍一放松,就撞到林大人的枪口上了。为捍卫文化纯洁性和神圣性,林则徐在政治上上纲上线,这就引起了党争。
林这一击,正是时候,道光帝刚去世,咸丰帝新立,新官上任尚且三把火,何况新帝?新帝第一把火就烧向穆彰阿,下《罪穆彰阿、耆英诏》: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
而言其罪责,则为“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其中之一,就是“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 ”,“其心阴险,实不可问”。
穆彰阿的门生遍于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多被他引用,号曰“穆党”。徐继畲是穆的门生,也在“穆党”之列,林之攻徐,似有此意。
徐回京,报告了林的死讯,帝问林则徐为人,他说,林为人忠正,可惜不明外情,致贻误事机。他没有像在家书里那样,说林“为名所累”。
于是,新帝发话了,说:徐继畲乃老成人,何谓欺诈?
刚好,新任闽浙总督裕泰上了奏折,奏曰:福州连日来,阴雨绵绵,神光寺屋漏逢雨,英人遍觅瓦匠,无有应者,无敢往者,已搬走了。
这样的结果,就是徐继畲“外示德意,阴加钳制”所致。
问题解决了,按常理,他该官复原职了,可偏不,先把他放到太仆寺去做个少卿吧。太仆寺掌马政,也就是管养马的,最高长官是太仆寺卿,为从三品,副长官是少卿,为正四品。他从“巡行天下,抚军按民”的从二品巡抚,一下就降到正四品去了,在官本位的政治文化里,这叫做“栽”了!
好一本《瀛环志略》
(1)他又被免职了
从封疆大吏,一下降到弼马温,徐继畲不以为意。
咸丰帝大概有些过意不去,怕他郁闷,就让他多发言。
果然,他就发言了,直来直去,上了一折《三渐宜防疏》。
“渐”,是防微杜渐之渐,哪“三渐”呢?一渐大兴土木,二渐纵欲过度,三渐堵塞言路,都针对皇帝。皇帝没怪他,反而予以嘉奖。同时,曾国藩也上了一折,让皇帝心里发堵,一气之下,就扔了,后来,才捡回来读。
也许是对他的补偿,皇帝派了美差,让他入川主持乡试。
西行入川,一路风光壮丽,所见所感,与曾国藩相似。
可结局相异,曾国藩从四川主持乡试归来,便扶摇直上,而他却再次被人攻讦。还在四川时,徐继畲就接到了免职通知,独怆然而归矣。
这一次,就难以归咎于“穆党”了,因为曾国藩亦出自穆的门下,而际遇正相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遭到几乎整个官场的围剿呢?
就因为他写了一本书。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2)把天朝放下来
这本书,是道光帝要他写的,奉旨而作。
当年,道光帝曾向他垂询海外形势、各国风情,他知无不言,一一应对,道光帝听了,就说,你写本书吧。皇帝这样说了,他就写。
从1843年开始写,写了大约有5年时间,到了1848年,书就在福州刻出来了。他没有先呈交皇上审阅,由皇上钦定是否出书。
他是抚台大人,在福州出的初刻本,就叫做“抚署”本。
书刻出来,整整有两年了,都没有呈给皇上,为什么?
也许是他不再奉旨了,求知的热情压倒了奉旨的忠诚。
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畲诞辰二百周年》一文指出,徐氏本人对地理学研究颇有造诣,在传统舆地考证方面有《尧都辨》、《晋国初封考》、《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汉志沿边十郡考略》等著作。
真正的学人,骨子里,大抵都有“独立之精神”,以此“独立之精神”治学,而有“自由之思想”,以“自由之思想 ”写书,没有必要奉旨。
更没必要呈奏皇上,跑到皇上跟前去,哪壶不开提哪壶。
徐氏《瀛环志略》以“自识”开宗明义,云:“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天下观里的《华夷图》和《广舆图》,就是“以意为伸缩”的,因而不可靠,不可取,而“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取舍之间,立场已明。
其言成书,则曰得“西国多闻之士,能作闽语”的“米利坚人雅裨理助”。雅氏“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徐继畲“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此后,反复搜求,“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 “考证”二字,道出学术来历,从考据学来,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乃考据学真谛,学人奉行,高于圣旨。故徐氏,初以奉旨制夷著书,但热血沸腾之余,亦要根据材料说话,结果,有违初衷。
全书,自始至终,“依图立说”,不言制夷。而《海国图志》迥异,魏源从公羊学来,以公羊学撰《海国图志》,非为求知,为的是制夷。制夷之知,如“知彼知己”,还待在兵法里。魏源为皇朝经世,而著《海国图志》。
就学术价值而言,《瀛环志略》明显要高于《海国图志》,周振鹤的文章,从两个方面指出了这一点。一是就材料而言,《瀛环志略》所据材料,都是经过考证的,而《海国图志》则是材料汇编;二是就思想而论,《海国图志》的中心思想是制夷,还在天下观的范畴里,而《瀛环志略》则走出了天下观。
周的观点,当然是用了现代性的眼光来看,如果从传统上来看,士人的价值偏好,还是会倾向于《海国图志》,而视《瀛环志略》为异端。
亏了有清一朝,对于督抚刻书,没有审查制度,所以,怎么写,就怎么出。书一问世,就招来了一片非议,政敌以此攻击徐氏,自是不必说了,就连他的好友也批评他失了“夷夏之大防”,混淆了“内外有别”的大义。
书还未刻完,他就将已刻好的头三卷请张穆看,张穆读后,复信,赞扬此书,考据之精,文词之美,为“海国破荒之作”。同时,又批评他把“皇清一统舆图”置于亚洲总图之下,建议他将本朝舆图放在亚细亚图上面。
张穆说:春秋体例,严于内外二字,要从华夷之辨上来谈海外异闻。谈到各国信史时,最好用存疑口气,不要像明朝徐光启、李之藻那样,亦步亦趋,“遂而负谤至今。”
张穆是地理学家,用地理的眼光,他赞美了《瀛环志略》。可他还是理学家,用天理的眼光,他指出《瀛环志略》的危险性,并及时提醒。
张穆,字石州,时有大名,人称“为文不经石州呵斥订正,未可示人”。阅《海国图志》,他提供地理图示,读《瀛环志略》,他以天理提示。
天理束缚地理,造成认识盲区,以此可知,有清一代,对世界的认识,较之明代徐、李,倒退何止千里!一代名士,著名地理学家,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只有徐氏例外,从天下观里走出来,进入地缘政治新世界。
政敌断章取义,以他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故意将“西方”二字隐去,欲将其置于死地也就罢了,就连曾国藩,也说他的书“颇张大英
大禹治水算中国历史故事吗
夷”。这在当时,是一顶不小的帽子,虽非卖国,也算崇洋媚外了。徐氏怎样 “张大英夷”?试与《海国图志》一比。“海国”,乃相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之外,都是海国。“海国”的提出,是天下观的新发展,将天下分为中国和海国,天朝居中国,四夷居海国,所以《海国图志》无中国,以示天朝不与四夷为伍。
在《海国图志》里,只要谈到外国,统统一“夷”以蔽之。
周振鹤指出,在甲辰稿《瀛环考略》里,徐氏还一仍旧贯,以夷为说,或曰“英夷劲兵”,又曰“英夷商舶”,至《瀛环志略》初刻,始改之。
因此,《瀛环志略》里,已不分华夷,改称英夷为英吉利,改称英国领事为英官,而不再叫做英酋,除了引用他人之语,徐氏很少用“夷”字。
除了《海国图志》,魏源还著有《圣武记》,这两本代表作,一本讲述了天朝以“圣武”经营中国,另一本直指当下,欲以“圣武”经营海国。
这两本书,加上他那套《皇朝经世文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帝王学体系。在帝王学体系内,制夷,与其说是爱国主义,毋宁说是王权主义。
更何况以世界为“海国”,显然忽悠了地理常识。与“中国—海国”的说法相应,就难免要将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削足适履,划在“北洋”国里。
而《瀛环志略》,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瀛环”不是天下,而是对地球上水地关系的描述。该书,开篇就写地球,指出,地球表面水土分布,“海得十之六有奇,土不及十之四”,陆地被海洋环绕,这就是所谓“瀛环”。
“瀛环”二字,由徐氏发明,以前未见用,颇有海权意味。“瀛”即海,瀛所环者即列国,故《瀛环志略》,乃列国志也。“瀛环”中,海大于陆,水多于土,各国来往,亦多行于海上,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控制海洋。
“瀛环”乃世界,而非天下,列国自有主权,不属于“王土”。
世界有四个洲,欧罗巴最强,亚细亚最大,而中国居其一。
中国,为亚细亚第一大国,并非“瀛环”最大国。“瀛环”最大国是俄罗斯,最强国是英吉利,它们对中国威胁最大。而新兴的米利坚国却打败了英吉利,于是,徐氏希望中国向米利坚学习,能像米利坚那样,打败英吉利。
联美抗英!一个以主权国家自立于世的海权思想萌芽了……
这对于一位曾参与抗英战争的老兵来说,恰如水到渠成一般,虽然有些一厢情愿,但其战略眼光何等高远!今天来看,联美依然任重道远。
(3)赞美华盛顿
徐氏《瀛环志略》,一提起美国,就会联想到中国:
“米利坚各国,天时和正,迤北似燕晋,迤南似江浙。”
在按语里,他又以充满热情的笔调,写道:“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万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
这样将美国与中国相提并论,哪还有什么夷夏之大防?
更有甚者,他还将“三代之治”与华盛顿治国相提并论:
“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
所谓“胜、广”,乃陈胜、吴广;而“曹、刘”,则曹操、刘备是也。此数人者,或起于草莽,为起义之领袖;或拥兵一方,为割据之王。
徐氏将他们一一拿来,与华盛顿相比较,发现华盛顿一人,就兼有了此数人的特质,而气象格局尤胜之。“提三尺剑 ”,起兵于民间,“开疆万
讲中国历史故事的好书
里”,此乃开国帝王汉高祖刘邦形象,与华氏何其相似,而华氏尤胜之。何也?因其“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而开民主之国也!且以“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之和平精神立共和之国也。徐氏将华盛顿放到中国历史上来理解,认为华氏超越了自秦汉以来所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可以直追三代圣王。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史观里,真可谓登峰造极了。因为圣王,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可望不可即的理想。
耐人寻味的是,他没有将这样的评价奉献给中国皇帝,却无比慷慨地赠与了美国总统,观华氏画像,便一见倾心,叹为“雄毅绝伦”。何也?中国人爱谈“天下为公”,可从周公、孔夫子以来,“天下为公”在中国,还停留于话语,而华氏却将它坐实;儒生神往“三代之遗意”,而华氏却使它成了国体。
徐氏指出,“美国合众以为国,疆土万里,国事付之民议”,此乃华盛顿,“创古今未有之局”,“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周振鹤说,这两段按语,在甲辰本《考略》里就有了,《志略》一字未改,初稿曾将“几于天下为公”一句删去,后又在旁边重写,加了圈点。
徐继畲敢这样写,在当时需要勇气。这勇气,来自实事求是,亦来自他灵魂深处觉醒了的自由意志。他赞美华盛顿时,提到了曹操和陈胜,这两人,或为乱臣,或曰贼子,可他爱屋及乌,推崇华氏,顺便也将他们提起。
为此,他被罢官,回到老家,长叹曰:我由太守历封疆,外任十六年,归来一贫如洗,老病笔耕。于是,有人请他到平遥去主持一所书院。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在南方蔓延,捻军也在中原兴起,又有人请他去办团练。
罢官以后,其书被禁,可书的影响还在。185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推荐,将赞美华氏的那两段话,立石刻碑,送到美国,镶嵌在华氏纪念塔内。
此碑落款:“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辈立石,合众国传教士识。”这位刻石的宁波知府,名叫毕永绍,上任不到一年,就干了这么件离谱的事,此事一办完,就离职了。有人说,毕氏名义上是离职,实为罢免。
出了这样的事,离职和罢免都不足为怪,奇怪的是,毕氏为什么要那样做。他是基督徒吗?这样的可能性很小。他是徐继畲的门生?有可能,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此事发生前,他大概也没有征求过徐氏的意见。
这块石碑运抵美国后,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了英文,于是,碑文就在美国传播开来,美国人知道了,东方有位徐大人,如此赞扬美国。
任复兴先生在“徐氏坐标及中国的巽股定位——《敦艮斋遗书》、《瀛环志略》合读”一文中指出,1848年,处于欧亚大陆西北的托克维尔,和欧亚大陆东南的徐继畲,分别将他们热情的目光,同时投向了美国。
一个东方人和一个西方人,站在他们各自祖国的立场上,异口同声地赞扬美国,使美国人更加坚信,美利坚的立国主张和理想具有普世性。
正是这两人,使美国人大吃一惊地发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那时,托克维尔还是一位漫游美国的法国青年,回国以后,写了一本《论美国的民主》,要法国向美国学习,预言了普世化的民主制度。
而徐继畲则是抗英前线一名老兵,他在对祖国安危的焦虑中看世界,从中发现了美国。当时,他最关心的问题是,美国凭什么打败了英国?
从华盛顿身上,他看到了“几于天下为公”的力量,这力量的源泉,就是“国事付之民议”的民主制度,来自“三代之遗意”的自由思想。
徐氏被皇上贬回老家了,而皇上则被洋人撵出了北京。皇上驾崩前,一番痛思,想要扭转乾坤。他不能扭转夷人,就只好扭转自己,使自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一转,臣下跟着都转,纷纷从主战转向主和了。
这样一转,便转出了个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京城,以恭亲王奕为代表,在地方,以两江总督曾国藩为代表。当年曾国藩读《瀛环志略》,曾批评徐氏“张大夷人”、“夸张夷情”,而今重读《瀛环志略》,他就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对于各国之名都茫然无知,更别说各国的国情了。而恭亲王奕,由于正在筹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就请徐氏来总理衙门行走并兼管同文馆。
从罢官到复职,熬了十几个年头,熬得徐氏更加无畏了。
1867年,美国公使蒲安臣奉总统之命,将华盛顿画像作为国家礼物送给他。在赠像仪式上,徐氏作了答辞:华盛顿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连接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
这样的答辞,纯属徐氏个人口吻,不是官方口径。过了从心所欲之年,历尽磨难以后,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当着驴夸千里马,驴恼吗?
后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在中国之影响》一文,着重介绍了《瀛环志略》及徐氏本人,对于徐氏复职,认为是美国在中国影响所致。同时,该报还发表了蒲安臣致辞和徐氏答辞,可见美国舆论对此事的重视。
(4)书的影响
时过境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重印了《瀛环志略》。
这回出的不是抚署本,而是总理衙门本。总理衙门本没有删节,也没有要求徐继畲修改,就作为同文馆教科书出了,是病急乱投医?
想当年,在福州出初刻本时,“甫一付梓,即腾谤议”。
谤议之尤者,为李慈铭,斥曰:轻信夷书,夸张外夷,尤伤国体。连好谈洋务的郭嵩焘都不以为然,以为徐氏难免张大夷人,夸张夷情。
即便如此,人们依然争相阅读。道咸间,读过此书的内外大臣,有祁隽藻、吴文镕、董恂、曾国藩等人。尤为难得的是,刘韵珂、刘鸿翱、彭蕴章等,竟然以一、二品大员身份,为书作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他们虽然赞扬了徐氏书,但依然是在天下观里来赞扬的。刘鸿翱序云:“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 ……我朝幅员之广,亘古无二。中华十八省外,南极越南,北极俄罗斯,东极朝鲜,西极雪山、葱岭,几得亚细亚之全土。” 与天下观迥异的那部分,他们就视而不见,只当是隐恶了。
刘鸿翱夸徐氏书,贬《海国图志》,与李慈铭正好相反。李责徐氏于天下观失防——“以夷变夏”,刘鸿翱则斥《海国图志》于史地无稽。
然而,1852年,魏源重印百卷本《海国图志》,就大量引用了徐氏书,以补救之。刘鸿翱所了解的《海国图志》,很可能是在这以前刊出的。
而徐氏书,自总理衙门本问世,便具有了官方性质,以至于官员出国,人
中国历史五部爱情神话故事
手一册。自总理衙门设置以来,清朝派人陆续出使欧洲,1867年有斌椿,1875年有黎庶昌,1876年有郭嵩焘,1890年有薛福成,他们都随身带了《瀛环志略》,沿途作为参照,并加以考核。黎庶昌《西洋杂志》赞道:“所经过山川城市,风土人情,《瀛环志略》所载,十得七八,乃叹徐氏立言之非谬”。而有“中土西来第一人”之称的斌椿,在《乘槎笔记》中,也这样写道:“自古未通中国,载籍不能考证,惟据各国所译地图,参酌考订,而宗以《瀛环志略》耳。”这样的评价,郭嵩焘起初不信,出使英国以后,始叹服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乎!
有人在研读《瀛环志略》的同时,开始了续补、增订工作。咸丰年间,就有何秋涛作《〈瀛环志略〉辨正》,对有关俄罗斯记述的错漏处作了订正,到了光绪年间,“订误”和“续集”更是层出不穷,薛福成也出了本《续瀛环志略》。
后来,康有为也读了《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还对两书进行了比较。他在《桂学答问》中指出:“《瀛环志略》其译音及地名最正,今制造局书皆本焉。《海国图志》多谬误,不可从。”梁启超《三十自述》言其赴京会试,下第归,途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
进入20世纪以后,徐氏在革命化的史观里逐渐被人淡忘。到了世纪末,1997年5月的一天,在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上,举行了一个特别的纪念仪式,纪念徐继畲诞辰二百周年,此时,正好是《瀛环志略》问世150周年。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从我居住的华盛顿特区白宫的窗口向外眺望,我们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俯视全城。那是一座高耸的方形尖塔。在这个庞大的纪念碑旁,有一块很小的石碑,上面刻着的碑文是:美国决不设置贵族和皇室头衔,也不建立世袭制度,国家事务由舆论公决,美国就是这样建立了一个从古至今史无前例的崭新政治体系,这是最奇妙的事物。
这些话不是美国人写的。克林顿又提到了徐继畲……
附注:
天下观,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中国,就是王土。
《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无边,王权无限,是以中国为主体不断扩展的中国化的人民与土地相结合而统归于王权的政治地理空间。
正所谓“王道荡荡,没有边疆,道之所在,即为国界”,因此,以王权行王道而制天下,建立大一统国家,便是一代王朝的最高理想。
天下观有“华夷之辨”,“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宋人石介著《中国论》说:天在上,地在下,居天地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这样“辨”的目的,是要“以夏变夷”,而非“以夷变夏”。
华有攻夷、治夷的权力,而夷只有朝贡的义务,天下观里无外交,只有主宰和被主宰的关系,中国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中心,是主宰者。
在天下观的地图里,天圆地方,“中国”最大,居于天下之中央,四围是海,海外有些岛国,环绕之,归化之。宋代《华夷图》和《广舆图》,都将中国画得很大,而四夷则微乎其微,模糊不清,连海洋都成了中国的护城河。
清人还在《中国论》和《华夷图》里自得其乐,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到魏源《海国图志》,一路行来,行到徐继畲,才开始走出天下观。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2/29/563810.html
以上是关于影响近代历史进程思想巨匠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影响近代历史进程思想巨匠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18532.html。
猜你喜欢
- 闻仲历史原型是谁,比干 2023-10-01
- 汪精卫-汪精卫的坟墓为何会被炸开?这其中有着什么原因? 2023-10-13
- 三十六计-三十六计之打草惊蛇的原文意思和故事典故 2023-08-14
- 调虎离山-三十六计之调虎离山的原文意思和故事典故 2023-08-14
- 军事历史-二战日军如何对待无法行走的伤兵 2023-08-14
- 骷髅-二战哪个师最能打,苏联人恨到将其赶尽杀绝 2023-08-14
- 军事历史-假如二战德军和日军打起来谁厉害 2023-08-14
- 莫斯科保卫战-苏联从远东调运多少部队加入莫斯科保卫战 2023-08-14
- 宣太后-春申君与芈月的关系是怎样的?其实俩人都没见过面 2023-08-14
- 妲己-纣王为什么那么爱妲己?只因两个原因无人能及 2023-0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