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
博物,考古

- 中国历史故事-小虎历史故事网
- 2023-08-30 03:09
- 小虎历史故事网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內容提要:在漢晉畫像的倉廩圖中,人、物之組合,特別是人與糧倉、量器之組合,展現了“糧食出納”的場景。畫面裏那些被人握在手中的細棍和束狀之物,很可能是用來記錄糧食出納的券或簡札,統稱為簡牘。將圖像、考古實物、文獻與簡牘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可以加深對相關制度的瞭解,進一步認識簡牘時代。
關鍵詞:漢晉畫像 倉廩圖 簡牘 券 糧倉 量器
我們現今所見到的漢晉畫像,主要來自墓葬中的壁畫、畫像石和畫像磚等。它們的數量頗不算少,非常值得研究。這些畫像不僅有一般考古資料的長處,屬於第一手的史料;且獨具特質,能夠記錄並呈現古人所見所思的場景,直觀而生動。儘管這些場景或有誇飾的成份,但因其本原在古人之心目,故自有依據和道理。
在畫像中,各色人、物等可容納於一幅畫面。這些人、物等被組合起來,一同出現,就構成了場景。通過對場景中群像的直接觀察,我們可以較爲清楚地辨認它們,了解它們之間的關係。由此,又可進而探索其組合與出現的意義,獲取更多層次的信息。這樣的作用,是別種考古資料(如單個的器物)所難以提供的,也是文字資料所難以企及的。
漢晉畫像裏往往有重複出現的題材,即所謂“母題”,大概與這些畫像的來源相近有關。“倉廩圖”就是這樣的題材。墓葬中的倉廩圖或有享祀和祈福的含義,這裏不對此做深入的探討。本文擬就漢晉畫像裏的倉廩圖所展示的“糧食出納”場景進行考察,研究其中的糧倉、量器和簡牘,以期對相關的制度有更多的瞭解,進一步認識簡牘時代。
一
在漢晉畫像裏,往往可見到這樣的畫面:一座房屋或一組房屋,多較高大,或位置顯眼;房屋之前有榖堆、容器,有裝卸、搬運穀物之人;周遭或有車輛和歇息的牲畜,以及雞禽、鳥雀等。此類畫像,當可稱之爲“倉廩圖”。在有些倉廩圖裏,除上述內容外,還可見到這樣的景象:有人手握數根細棍或束狀之物,或正與他人交接,或正待交接,或坐守在房屋之旁。對於這種細棍或束狀之物,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見:或稱之為簡冊;[1]或稱之為算籌;[2]或僅稱之為“物”,[3]或將持棍人的畫像同整幅倉廩圖相割裂,加以另外的解釋;[4]或忽略不提。[5]以上意見皆有未安之處。筆者認爲,這些倉廩圖裏的各色人、物等,尤其是糧倉和量器,均表明畫面所呈現的是糧食出納的場景;與此相關聯,那些細棍和束狀之物則應是記錄糧食出納的券或簡札,統稱爲簡牘。現將有關的畫像列出,加以說明。
圖1:密縣打虎亭一號漢墓畫像石(白描綫圖)[6]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此爲河南省密縣打虎亭一號墓南耳室南壁的畫像石,1961年出土,是東漢遺物。《中國畫像石全集》題作“收租”。畫面的右部爲一重檐之樓,樓底有矮柱,樓側有梯,此應是糧倉。畫面中部上方,一著大袖長衣者坐席上,前置硯臺等物,其旁有一方形竹笥,其側爲糧堆。在此人面前,有一人跪地,雙手執束狀之物,似在向其禀告。在畫面的下部,有一容器置方墊上,其周圍有量糧者、裝糧者和糧車、糧袋等。此應是入糧場景。
圖2:廣漢東南鄉漢墓畫像磚[7]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此爲四川省廣漢市東南鄉漢墓的畫像磚,1984年出土,是東漢遺物。《中國畫像磚全集》題作“納糧畫像磚”。畫面中有一座建築,“四阿”式頂,屋底有柱,門敞開,此應是糧倉。房屋之前,一著大袖長衣者坐席上,手握數根細棍。畫面下部有兩個著短衣者,其中一人在量糧,正用手中的容器向
楹联中的中国历史故事作文
地上的容器傾倒,另一人正從車中取物。畫面中有二馬、二車,其中一馬套在車上,另一馬已卸載。此應是入糧場景。圖3:護烏桓校尉幕府穀倉(局部,摹本)[8]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此爲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漢墓之前室西壁的壁畫(局部),1971年發現,是東漢遺物。畫面中有一座重檐高樓,其底部有臺基。樓的一層有門和氣窗,二層爲氣樓。在牆壁上,題有“護烏桓校尉莫(幕)府穀倉”九字,知爲官府糧倉。畫面中有三人,一人肩負糧袋而來,一人在門口守候,另一人手持數根細棍坐在樓旁。此應是入糧場景。
圖4:長清大街村漢墓畫像石(局部)[9]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此為山東省濟南長清大街村漢墓畫像石,2005年出土,是東漢晚期遺物。[10]《山東省博物館館藏精品》一書題作“倉廩圖畫像石”。畫像石上有榜題“量榖”二字,知是計量穀物的畫面。因原圖較大,內容多,本文僅截取局部。在這裏,圖的左部為兩個圓形倉,倉頂有蓋,其一已打開,有二人守在倉旁。圖的中部為量榖之眾:一人剛從倉中取出糧食,手捧容器走來;一人手握數支細棍,在觀看放置地面的容器,該容器的外壁題有“斛”字,[11]知為量器;一人俯身立其對側,正將手中的容器向斛內傾倒,口銜一支條狀物或細棍;[12]另有兩人手捧容器離開,正走向屋舍,其容器中各插一細棍。圖的右部為屋舍,屋舍外有一人站立,內有兩人對坐交談。此應是自糧倉出糧場景。
圖5:敦煌佛爺廟灣M37號西晉墓彩繪磚[13]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此爲甘肅省敦煌佛爺廟灣M37號西晉墓之西壁北側的彩繪磚,1995年發現,是西晉遺物。《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一書將此圖分割成三部分:上部、中部合題爲“樓閣式倉廩”;下部之左,題爲“進食”;下部之右,題爲“牛、車”。[14]而實際上,這是由一組彩繪磚共同構成的倉廩圖:畫面上部是并排相連的兩個樓閣式建築,有瓦檐、欄杆;門的顏色爲左灰右紅,橫閂在外,上有門關。畫面中部似爲四根立柱[15],其間有兩個以條磚搭壘的小洞,內置榖粟,[16]可知此樓閣式建築確爲糧倉。倉門的顏色不同,或表示所儲之物不同。在畫面下部,左邊有兩人,其中一人年長,長鬚,著袍坐榻上,兩手各執數根細棍;另一人短鬚,著衫,雙手捧一容器走向前者。右邊有一車、一牛,車已卸載,長轅搭地;牛臥車旁,前面有一個食料筐。此應是入糧場景。
下爲M37號墓的橫剖視圖(局部),[17]可顯示圖5在墓室中的位置。在圖5的對側,即此剖視圖的左半部,也是一幅倉廩圖。該圖亦有糧倉,此外有糧堆和觀糧、捧糧之人等。我們或可將這左右對置的兩圖拼合起來觀看。拼合起來的兩圖,顯示出了它們彼此間的聯繫,構成了一幅更大的倉廩圖。[18]同單個小圖相比,大圖的內容更多,場景更豐富完整。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圖6:敦煌佛爺廟灣M39號西晉墓彩繪磚[19]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此爲甘肅省敦煌佛爺廟灣M39號西晉墓之西壁南側的彩繪磚,1995年發現,是西晉遺物。《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一書將此圖亦分割成三部分:上部、中部合題爲“樓閣式倉廩”;下部之左,題爲“撮糧”;下部之右,題爲“母童嬉戲”。[20]而其實此圖與圖5類似,也是由一組彩繪磚共同構成的倉廩圖。此圖的上部、中部與圖5幾乎完全一樣:兩個相連的樓閣式建築,有瓦檐、欄杆和橫閂在外的門,其下似爲立柱,柱間有放置榖粟的小洞。所不同者,圖5的樓閣有六門,而圖6僅四門;顏色亦有別,爲左紅右灰。在此圖的下部,左邊有一糧堆,一女子手捧容器回顧,一男子手持簸箕撮糧。右邊有三人,一人右手執數根細棍前行;一人爲兒童,正“騎竹馬”玩耍;另一人坐地上招呼兒童,似爲其母。此亦應是入糧場景。
下爲M39的橫剖視圖(局部),[21]可顯示圖6在墓室中的位置。在圖6 對側,即此剖視圖的右半部,也是一幅倉廩圖,繪有糧倉、牛車和雞禽。我們或亦可將這左右兩圖拼合起來,視爲一幅更大的倉廩圖。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以上幾幅圖中的建築,無論從其外觀還是從其在畫面中的意義看,都無疑是糧倉。古代的儲糧建築有多種。其中,倉、廩、京、庾、囷、廥和窖、窌、竇等在文獻中較爲多見。《廣雅·釋宮》:“京、庾、廩、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廩”又作“㐭”,亦儲糧之所。《說文·㐭部》:“㐭,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㐭而取之,故謂之㐭。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凡㐭之屬皆从㐭。廩,㐭或从广从禾。”據“回象屋形”,知廩亦方形,其特點是“有戶牖”。《詩經·周頌·豐年》:“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毛傳:“廩,所以藏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京”的本義是人工築起的高土堆,又指高大的方形糧倉。《說文·京部》:“京,人所爲絕高丘也。从高省,丨 象高形。”《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見建家京下方石。”《集解》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29]“京”與“囷”往往並提。《管子·輕重丁》:“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尹知章注:“大囷曰京。”[30]《急就篇》:“門戶井竈廡囷京。”顏師古注:“囷,圜倉也;京,方倉也。”[31]“京”字在甲骨文中作“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除上述幾種方形倉外,還有其它樣式的倉。“囷”是圓形倉。《說文·囗部》:“囷,廩之圜者。从禾,在囗中。圜謂之囷,方謂之京。”《釋名·釋宮室》:“囷,綣也,藏物繾綣束縛之也。”王先謙注:“禾在囗中亦是束縛之意。”[33]用竹子作的圓形倉稱作“篅”。《說文·竹部》:“篅,以判竹圜以盛穀也。从竹耑聲。”《釋名·釋宮室》:“囤,屯也,屯聚之也。”注引畢沅曰:“《說文》:𥫱,篅也,从竹屯聲。此囤乃俗字。”用草作的圓形倉稱作“圌”。《釋名·釋宮室》:“圌以草作之,團團然也。”[34]此外,“庾”是露天的儲糧之所。《詩經·小雅·楚茨》:“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毛傳:“露積曰庾。”[35]又《說文·广部》:“庾,水槽倉也。从广臾聲。一曰倉無屋者。”可知庾也指建在水邊的糧倉。“廥”是草秣的藏所。《說文·广部》:“廥,芻稁之藏也。从广會聲。”《後漢書·蘇章傳附不韋傳》:“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36]廥也用作倉的統稱。《管子·度地篇》:“虛牢獄,實廥倉。”[37]《睡虎地秦簡·效律》:“禾、芻稾積廥。”[38]以上都是地面上的建築。還有建在地面以下的倉,如窖、窌、竇等,茲不具述。[39]
對本文所討論的這6幅畫像中的建築進行辨認,可以看出:除圖4之外,其它圖中的建築都是方形倉(圖1、2、3、5、6);它們的底部都有臺基或立柱(圖3有臺基,圖1、2、5、6有足或高架);它們或有氣樓、[40]氣窗(圖1、3有氣樓,圖3有明顯的氣窗);或有曬臺(圖1、5、6)。[41]上述這些特徵,大致可以同文獻記載中的倉、廩、京對應。而倉、廩、京都是規模較大的糧倉,與囷、庾、廥等相比,其構造較爲複雜,功能較爲完備,外觀也更高大講究。這應是它們較多地出現在倉廩圖中的主要原因。至於圖4中的圓形倉,雖係無屋的囷、庾之類,規模不很大,但它們在原圖裏四座一列排開,其上方還有七個巨型的甕罐狀儲糧裝置,亦足以顯示富有。
在圖1、圖2、圖4、圖5、圖6中,都出現了計量穀物的量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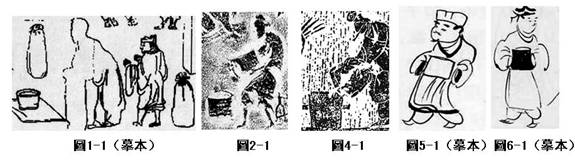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在圖1中,糧倉前,一圓口容器放置地面平攤的方形墊子上,其旁邊有糧袋和量榖人,故可確知此容器爲量器(見圖1—1)。《中國畫像石全集》的“圖版說明”稱此物爲“量斗”,[42]這是不正確的,因爲漢代的斗不會有這樣大(說詳後) 。在圖2中,糧倉前,一圓口容器放置地面,有人正用桶將馬車運來的糧食倒入該容器,知其當爲量器(見圖2—1)。以上兩圖中的量器,因其附近的建築具有明顯的糧倉特徵,且旁側有人在做量穀的動作,故不難判定。而圖4中放置地面的容器,前文已提到,因其外壁題有“斛”字,知是量器無疑。
圖5、圖6中的量器卻需仔細辨認。在圖5中,糧倉前,牛車、榖堆附近(參看前引M37號墓的橫剖視圖),一男子捧著容器走向坐榻上的年長者,雙手放在容器的中腰(見圖5—1)。《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一書認爲他們是主人和仆人,後者正“雙手捧樽趨前奉食”。該書並將繪有此二人的彩繪磚從其所屬的倉廩圖中分割出來,題作“進食”。[43]這是欠妥的。因爲坐榻上的人兩手皆握細棍,榻前無任何杯盤、食案等物,他的旁邊也沒有同坐者,不似畫像中通常所見的進食場景。而若將那個捧物而來的男子放到整幅倉廩圖裏進行觀察,便可看出他所捧的不是食具,而應是計量穀物的量器。[44]
在圖6中,糧倉前,榖堆和撮榖人附近,一女子捧著敞口的容器轉身回顧,雙手放在容器的中腰(見圖6—1)。《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一書認爲,該女子“雙手持樽”,是“農婦送飯后持食具歸去而戀顧農夫的生活場景”。[45]這一看法也是欠妥的。因爲該女子手中的容器,除顏色外,其外形和把持方式皆與圖5中男子手中的容器相像,故二者很可能是同一種物品。而若將該女子放到整幅倉廩圖裏進行觀察,便知她所捧的不是食具,亦應是計量穀物的量器。
《漢書·律曆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46]龠、合、升、斗、斛等皆量器,它們由小到大組成了“升斗斛”系列,除2龠等於1合外,都是10進制的等次關係。“石”在漢代除用作重量單位外,也用作容量單位,與斛同量。《淮南子·説林訓》:“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47]是“十石”等於“百斗”。《說苑·辨物》:“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48]是石同斛。《夢溪筆談·辯證》:“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已如此。”[49]漢晉簡牘資料裏有大量的糧食出納記錄,它們幾乎都以“升斗斛(石)”系列爲計量單位。蓋自秦統一度量衡以來,升、斗、斛(石)等便成爲各地普遍行用的糧食計量器具。到了後世,儘管其容積漸漸有變化,但名稱不改。王禎《農書》曰:“古有豆、區、釜、鍾、庾、秉之量。《左傳》曰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十釜爲鍾;又,二釜半爲庾,十六斛爲秉,皆古量之名也。今唯以升、斗、斛爲凖,最號簡要,蓋出納之司易會計也。” “今夫農家所得榖數,凡輸納於官,販鬻于市,積貯於家,多則斛,少則斗,零則升,又必槩以平之,貧富皆不可闕者。所謂出納之司,用至巨也。”[50]無論官府還是百姓,“升斗斛(石)”系列都是糧食出納所用的最重要的計量器具。
《說文·斗部》:“斛,十斗也。从斗角聲。”《廣雅·釋器》:“斛謂之鼓,方斛謂之桶。”王念孫疏證:“《曲禮》‘獻米者操量鼓’,鄭注:‘量鼓,量器名。’……《說文》:‘桶,木方,受六斗。’字通作甬。《月令》‘角斗甬’,鄭注云:‘甬,今斛也。’《呂氏春秋》、《淮南子》竝作‘桶’,《史記·商君傳》亦云‘平斗桶’。”[51]一般的斛容10斗,又叫“鼓”;另有方形的小斛容6斗,又叫“桶”;二者的容積之比是10:6。在漢簡資料中,有不少用量器“大石”、“小石”來計算糧食的記載,二者的容積之比也是10:6,[52]同斛與方斛之比。又《說文·斗部》:“𣂀,斛旁有𣂀,从斗𠩓聲。一曰突也,一曰利也。”《廣韻·蕭韻》:“𣂀,斗旁耳。” [53]可知斛的旁側有突出的“𣂀”。[54]《說文·斗部》:“斗,十升也。象形,有柄。”由“象形,有柄”看,斗有單柄。
現存的漢代銅斛數量不少,它們的容積大致爲20000毫升,皆圓筒狀,高約22—27厘米,口徑約32—37厘米。其中,“新莽銅嘉量”深22.9、口徑32.9厘米,中腰部有兩耳;[55]東漢“夷道官銅斛”高24.5、口徑34厘米,中腰部有兩個對稱的短柄。現存的漢代銅斗不多,其容積大致爲2000毫升,外形有方、有圓。方斗如新莽“始建國銅方斗”,高11、長14.75、寬14.77厘米,一側有柄;圓斗如東漢“元初大司農銅斗”,高7.8厘米,口徑20.3厘米,一側有耳。以上諸器皆有銘文,年代明確。[56]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新莽銅嘉量 夷道官銅斛 始建國銅方斗 元初大司農銅斗
我們將本文所討論的這幾幅倉廩圖中的量器與現存的漢代量器實物做對照,查看其大小和外形,便知它們不會是斗,而應當是斛,無論是大斛還是小斛。圖4中題有“斛”字的容器,則很可能是大斛。這些量器藉由不同時地的畫工之手,呈現在不同的糧食出納場景中,或粗或精,外形也不盡一致,但皆與文獻記載中的漢斗和現存的漢斗實物有較明顯的差別。換一個角度,如果從倉廩圖通常所使用的誇飾手法看,圖中的這些量器也不會是斗,而很可能是更大的量器——斛。
在“升斗斛(石)”系列中,斛(石)的容積最大,乃量之極。或許是由於如此大小的量器在漢晉時製作、使用較爲方便,適合進行各種有關糧食的計算,因而成爲當時最常用的糧食計算單位。例如,對農產量的計算、對人的月口糧的計算、對倉榖出入的計算,以及各種糧食交易與流通中的計算,乃至官吏俸祿的計算等,都普遍以斛(石)爲單位。而斗、升、合等,大多只用以計算零餘。不過要注意,這裏說的只是漢晉時的情況。在後世,“升斗斛(石)”等量器的容積逐漸增大,斛、石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到明清時,斗的容積已與漢晉時的小斛(石)接近,[57]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也明顯增多。而漢斗與此斗大有差異,不可不辨。
還應提到,在圖1中出現了幾個糧袋(見圖1—1)。漢代將包裝鹽、糧的囊袋叫作“帣”。《說文·巾部》:“帣,囊也。今鹽官三斛爲一帣。”又,《類篇·巾部》:“囊有底曰帣。”《廣韻·線韻》:“帣,囊也,亦三石爲一帣。”[58]“石”在此應是容量單位,其大小同“斛”。鹽官以三斛(石)爲一帣,糧食亦應同此標準。[59]
在漢簡中的例子,如:
入粟三石帣百九,又糜三石帣九十二奇一石
(《居延新簡》E.P.T56:120)[60]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84.27)
卒陳偃,粟一卷三斗三升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57.19)
士吏尹忠,穈一帣三斗三升自取,又二月食穈一帣三斗三升,卒陳襄取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57.20)
這幾條簡文都是用“三石帣”裝糧食的記載。簡文中的“卷”,通“帣”。帣(卷)在此處被用作粟和穈的計算單位。第一、二條是糧食出入的記錄,應同倉有關,未知其簡文中的“石”是大石還是小石。第三、第四條都是領取口糧的記錄,而吏卒的月口糧通常爲三小石有餘,[61]故簡文中的“一帣(卷)”相當於三小石,合兩大斛(石)。按此,當時用來裝糧食的帣,每帣至少可容兩大斛(石)。將圖1中的糧袋、量器相對比,可見二者的關係正與帣、斛的關係一致。此當可視爲圖1中的量器是斛的一個旁證。
二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幅倉廩圖中都出現了手執細棍或束狀之物的人: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在圖1中,手執束狀之物者正跪地向坐榻上的人禀告(見圖1—2);在圖4中,手執細棍者立斛旁,正觀看量榖情況(見圖4-2);在圖6中,手執細棍者似正從糧倉離開或正走向糧堆(見圖6—2及前引敦煌佛爺廟灣M39號墓的橫剖視圖)。這三人一跪、一立、一行,從其舉止和在場景中的位置看,他們都不會是糧倉的倉主或主管人,而應是經手辦事者。而在圖2、圖3、圖5中,手執細棍者皆安然而坐,在畫面中的體形也比較大,從其舉止和在場景中的位置看,他們應當是糧倉的倉主或主管人(見圖2—2、圖3—2、圖5—2及前引敦煌佛爺廟灣M37號墓的橫剖視圖)。
前文已提到,有人認爲圖1中跪地者手捧的束狀之物是簡冊。而圖像顯示,此物下端收緊,上端散開,不似簡冊。[62]而且,在糧食出納的現場,糧食出納的記錄大概也並不書於簡冊(說詳後)。此物應當是成束的券或簡札,且頗似未剖分的券(說詳後)。
前文還提到,有人將圖2、圖5中坐者手握的細棍當作算籌。然而無論從大小還是從使用方法看,算籌都與此有別。[63]用作算具的算籌,漢時稱爲“籌策”、“算”、“筭”。《史記·高祖本紀》:“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64]《漢書·律曆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65]《說文·竹部》:“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則算籌的形制爲徑1分,長6寸。漢尺1尺約23厘米,1分合0.23厘米,6寸合13.8厘米。按此,算籌是細小的圓竹棒,200餘枚乃爲一握。其長度不及人手,比普通的券、簡札和簡冊要短得多。出土實物亦證明了這一點。在20世紀50—80年代出土的11批戰國至東漢的算具類算籌中,長度爲14厘米以下的佔了絕大多數。[66]不僅如此,算籌在其發展過程中還呈現縮短的趨勢。例如石家莊東漢墓出土的算籌,長度爲7.8—8.9厘米,約合漢尺3.4—3.9寸。[67]北周甄鸞《數術記遺》:“今之常算者也,以竹爲之,長四寸,以放四時;方三分,以象三才。”[68]按北周尺長約24.5厘米,4寸合9.8厘米。《隋書·律暦志》:“其算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策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69]按隋尺長約29.5厘米,3寸合8.85厘米。算籌的長度縮短,可以減少布算所需的平面,更便於進行複雜的計算。[70]
在使用算籌時,要將算籌布放在平面上,用積算的辦法記數,縱橫相間、自左向右地擺列。據學者研究,進行一般的四則運算,大約需要二三十枚算籌和辦公桌大小的地方。[71]還有學者認爲,用算籌進行運算需要使用畫有方格的算盤。[72]
因算籌細小,數量又多,故通常被裝入囊袋。如:
錦帬一 筭囊一 卮一合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遣策,簡二)[73]
君兄繒方緹中物疏:
方緹一●
刀二枚
筆二枚
管及衣各一
板研一
筭及衣二
(尹灣漢墓簡牘,木牘一三正)[74]
以上兩條簡文中的“筭囊”和“筭及衣”之“衣”,都是盛放“筭”的囊袋。這種囊袋往往被人繋在腰間攜帶。例如,陝西千陽縣西漢墓發現的31枚骨算籌,出土時“裹在一絲絹囊內,繋在死者腰部”,與帶鉤同出,研究者稱之爲“算袋”[75]。又,石家莊東漢墓發現的30枚骨算籌,“位於墓底中部,骨架上面,說明入葬時佩帶在腰部,但是否有算袋,已無法辨認”。[76]將算籌的這些情況與圖2、圖5對比,可知都不能相合;與另外幾圖對比,也是如此。
那些被人握在手中的細棍或束狀之物應與糧食出納的手續相關。凡稍具規模的糧倉,糧食出納皆須記錄。一方面,糧倉的管理者要作賬;另一方面,參與出納手續的各方要取得相應的憑證。在簡牘時代,這些出納記錄往往以“券”的形式來書寫。[77]如:
■卅年四月盡九月倉曹當計禾稼出入券以計及縣相付受
廷 第甲
(里耶秦簡⑧774)[78]
中倉券也(A面)
南山鄕嗇夫租券本也(B面)
(東牌楼漢簡105A、B)[79]
以上兩簡實際上都是楬,即簽牌,原當附於相應的文檔。前者為秦時之物,其頂部塗黑,上段有兩個穿繩用的小孔。該楬應與“倉曹”的“禾稼出入券”有關。後者為東漢末年之物,其頂部未塗黑,上段兩側各有一綁繩用的契口。該楬與“中倉”的券有關,此“中倉”應是儲藏租糧的官倉。“租券”可能是記錄租糧出入的券,“租券本”則可能是指所收存的租券之半券,略似後人所謂“券根”。
在各類遺址所出的簡牘文書中,常有數量可觀的券。例如,在里耶秦簡中,記錄錢、糧、物出入的券佔了這批簡牘總數的十分之一以上。[80]在三國吳簡中,不僅有數量龐大的木券《嘉禾吏民田家莂》,其竹簡中的券亦比比皆是,它們的內容幾乎都與倉庫出納事務有關。在西北邊地漢簡和樓蘭晉簡中,券的數量也不算少。這是一個頗值得留意的現象。
在紙之前,簡牘是最主要的文字載體。和紙相比,簡牘既厚又硬,不能夠複寫、按指紋,也不便於蓋印章。需要蓋印章的簡牘,須預先在木、竹材料上挖制泥槽,在槽中填泥,然後才可以在泥上抑印。[81]此法費時費力,且其印文易模糊,泥塊易破損脫落,又難以蓋騎縫章,這就限制了印章的使用。因此,在今日可通過複寫、按指紋和蓋印章等方法來製作和認證的一些憑證,在簡牘時代往往採用剖分符、券的形式。[82]其方法大致是:將某憑證剖開,分成可比對的、同樣的兩份(或兩份以上[83]),由有關的諸方各執其一,以對合爲信。符是證明某種身份、權力或執行某項任務的信物,因與本文無涉,不贅述。券則應用範圍較廣,可作多種憑證,如債務契約、買賣合同、收支憑據、核校清單等。
人們在立約時,先在券上書寫文字,然後將券體剖分。其右半歸給與方或債權方,左半歸接受方或債務方,以爲憑證。[84]《禮記·曲禮》:“獻粟者執右契。”鄭氏注:“契,券要也,右為尊。”孔穎達疏:“粟,粱稻之屬也。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鄭注此云‘契,券要也,右為尊’,以先書為尊故也。”[85]券通常以木、竹爲材,長度約一漢尺,但亦有更長者。[86]未剖分的券,其厚度或寬度略大於普通的簡札,以供分割。人們也預先製作券體大半剖開而下端相連、留有空白的券,以便使用。例如: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這是1枚預先製作以待使用的木券,出土於懸泉置遺址。該木券從上至下、正背縱剖,券體大半剖開而下端相連,正、背面皆有墨跡。[87]其釋文是:
【正面】出粟 元始元年正月 縣泉置嗇夫就付
【背面】入粟 元始元年正月
釋文顯示,該木券當用於糧食出納。其紀年是元始元年(公元1年),爲西漢平帝紀年。它的正面記錄“出粟”,剖分後當爲右券;背面記錄“入粟”,剖分後當爲左券。“出粟”、“入粟”之下留有空白,可知是預備使用之券。使用時,當在“出粟”、“入粟”之下加填數額,並在券上寫明糧食出納手續中各方參與者之名,將券體完全剖分。
券的剖面可用來比對,但仍嫌不足,還需要其它的方法加以補充。《說文·刀部》:“券,契也。从刀,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在今存的刻齒券(契券)中,有不少是債務契約和買賣合同,主要見於私人之間的借貸和交易等。立券者務求確認券之左右,務求契約、合同中的數字不被竄改,故用此左右分明、可用刻齒表示數字的刻齒券。刻齒券亦有用作會計憑證者。今存的同文券(莂、傅別)則幾乎全部是會計憑證,見於官府與百姓之間、官府與官府之間的經濟活動,如賦稅繳納、錢榖出入、物資盤點等。其形式和功能,同今日的一式兩聯、三聯單相仿,是收付、記賬與審核的憑證。或因這些憑證多行於官府,又繁雜量大,故用此相對便捷的同文券。但要指出,同文券在秦簡中尚未見,在漢簡中較爲少見,在三國吳簡和晉簡中卻數量很多。由此推測,它的流行的時間或相對稍晚。[91]
簡牘的使用年代相當漫長。漢時雖出現了紙,但簡牘並沒有被迅即淘汰,而是繼續使用,與紙共存了數百年。《初學記》載《桓玄偽事》:“古無帋,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92]王國維曰:“至版牘之廢,則尚在其後。”[93]可知在4世紀末的東晉中期,人們仍使用簡牘,經統治者頒令後才逐漸廢止。
剖分後的券,其外觀爲細長條狀,與單枚的簡札相仿。漢晉畫像中有一疑似“分券”的例子,見圖4-3: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圖4-3
此為長清大街村漢墓畫像石之倉廩圖的局部(圖4右部)。圖中,二人著大袖袍服,像是小吏,正對坐交談,手中似各握一支大小相同的細棍。從對本圖和圖4全圖的觀察和分析看,此二人手握之物很可能是券。他們像是在辦理出糧手續,結算甫畢並已分券,故各執其一。然而因畫像本身不夠清晰,加之筆者的認識有限,尚未敢遽定。
券在簡牘實物中的例子甚多,如: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1】出穈三石二斗 征和三年八月戊戌朔己未,第二亭長舒付屬國百長千長
(居延漢簡148.1+148.42,長26.3、寬1.1厘米,木質)[94]
【2】(A面)入粟小石?卌一石六斗六升大 □陽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B面)出粟小石?卌一石六斗六升大 □□陽朔三年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居延漢簡8.5A、B,殘長10.3厘米,寬1.0厘米,木質)[95]
【3】(A面)城北候長竇何,十一月食一斛五斗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B面)城北候長竇何,十一月食一斛五斗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居延新簡E.P.T65:8A、B,長22.7、寬1.2厘米,木質)[96]
【4】入西鄉嘉禾二年稅米廿一斛四斗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363,長28.3、寬1.2厘米,竹質)[97]
【5】入西郷司馬黄松嘉禾二年限米六斛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699,長27.3、寬1厘米,竹質)[98]
【6】出𢇲卌一斛七斗六升,給稟將尹宜部兵胡皮鸞十二人,人日食一斗二升,起十月十一日,盡十一月十日。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樓蘭簡紙文書集成》孔木50,長24.5、寬1.4厘米,木質)[99]
【7】入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樓蘭簡紙文書集成》沙木728,長 23.6、寬1.3厘米,木質)[100]
這些例子都是糧食出納的記錄。【1】的紀年是“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用西漢武帝年號。這是一條“出穈”的記錄。其上段右側有多個刻齒,[101]可知是一件刻齒券之右券。因未見其背面、側面的照片圖版,剖分方式不詳。【2】的紀年爲“陽朔三年”(公元前24年),用西漢成帝年號。這是一條關於“入粟”、“出粟”的記錄。其正、背(A、B)兩面的文字相同,僅有“入”、“出”之別,可知是一件尚未剖分的券,可從側面縱剖爲二。其殘缺較甚,未見可用以比對的刻齒或墨書的同文標記。【3】雖無紀年,但據《居延新簡》E.P.F22:440所載“甲渠塞候長居延肩水里公乘竇何年卅五,始建國天鳳上戊五年正月丁丑除”,知“候長竇何”的活動時間大致在新莽天鳳五年(公元18年)至東漢光武帝建武初期。這是一條領取廩食的記錄,其正、背(A、B)兩面的文字完全相同。在其中腰偏下,時間和人名之前,有墨書的“同”字標記的左半,可知是一件同文券之左券,係從正面縱向剖分而得。在券的末尾,有表示已經支取的押記“卩”。【4】的紀年是“嘉禾二年”(公元233年),用三國時期吳大帝孫權年號。這是一條納入“稅米”的記錄。在其上三分之一段偏下處,有墨書的標記“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還有些糧食出納記錄書寫在單枚的簡札上。“簡”是經過修治的細竹條,細木條則稱作“札”,它們的長度通常爲1漢尺(約23厘米)。例如: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8】入穈小石十四石五斗,始元二年十一月戊戌朔戊戌,第二亭長舒受代田倉監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居延漢簡273.24,長23.3、寬1.2厘米,木質)[102]
【9】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居延漢簡273.8,殘長22.5厘米,寬1.0厘米,木質)[103]
【10】入粟大石五十石,車二兩,輸吞遠隊倉 始建國天鳳一年三月乙丑,將輸守尉尊□□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居延新簡E.P.T65:412,殘長16.2厘米,寬1.1厘米,木質)[104]
【11】入穀五千五百二斛 受城倉 吏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居延新簡E.P.T27:11,殘長18.8厘米,寬1.1厘米,木質)[105]
【12】入黃龍三年佃卒限米□斛二斗一升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140,長21.8、寬0.8厘米,竹質)[106]
【13】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嘉禾元年稅吳平斛米八十六斛四斗,爲稟斛米九十斛邸閣右郎中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3845,長23.9、寬0.8厘米,竹質)[107]
【8】、【9】的紀年爲“始元二年”、“始元三年”(公元前85年、公元前84年),用西漢昭帝年號。此爲“第二亭長舒”自“代田倉”和“斥胡倉”領取糧食的記錄。文中不僅有領糧的數量、品種、日期,還記錄了糧食出納手續中各方參與者之名。【10】的紀年是“始建國天鳳一年”(公元14年),用新莽年號。此爲使用車輛輸糧入倉的記錄。【11】殘斷較甚,簡文內容不完整。其所載糧食的數量較大,頗似納糧入倉的記錄,但也有可能是某官署自城倉領糧的賬目統計。【12】的紀年是“黃龍三年”(公元231年),用三國時期吳大帝孫權年號。此爲納入“佃卒限米”的記錄。【13】的紀年是“嘉禾元年”(公元232年),亦用三國時期吳大帝孫權年號。此爲輸出倉米的記錄。在“領”字和“斗”字之下有繩痕。[108]
也有的單枚簡札可能是籌子。籌子,即籌碼、籌籤,在物、錢的出納過程中使用,可代表一定的數額,以便計算與核驗。古人將此物叫作籌。《說文·竹部》:“籌,壺矢也。”徐鍇繫傳:“投壺之矢也。其制似箸,人以之算數也。”[109]《急就篇》:“筆研籌筭膏火燭。”顏師古注:“籌,所以付與。”[110],籌可能源於投壺之矢;其形若箸,為細棍狀;可用於計數“付與”。應當指出的是,這裏所說的籌,與前文討論過的算籌(即漢時的筭、算、籌策)是不同的,兩者在外觀、用法上皆有差別。籌為扁平條狀或細棍狀,可表示物、錢等。一籌為一個計算單位,其上多寫有一定的數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皆記載,漢時常以“算”為計算單位,[111]籌或可視作“算”的實物形式。而算籌則如前所述,頗為細小,是布算用的算具,其上一般不寫字。
關於籌的用法,可參看圖4長清大街村漢墓畫像石。為了更清楚地討論,這裏再回顧一下這幅倉廩圖中部的畫面(從開啟的糧倉之右至屋舍前立者之左)。左起,第一人是領糧者,剛從倉中取出榖,正要量榖,其手中、容器中皆無細棍;第二人是主持量榖者,也是發放細棍者,其手握一束細棍;第三人有可能也是主持量榖者(或是領糧者),正在量榖,其口銜一支條狀物(或細棍);第四、第五人是領糧者,量榖已畢,其容器中各插一支細棍。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個領糧者手持的容器大小相仿,其細棍則經由量榖而得。從該圖所示細棍的發放方式、領糧者容器的大小相仿等情況看,那些細棍應當代表了某一數額的糧食,其上或有標識,以便計算、核驗。因此,它們很有可能是籌。
前文提到,圖4的榜題為“量榖”,實際上該畫面或亦可稱作“量籌”。《建康實録》巻十二:“道濟夜頓,命軍中高唱量沙,散布餘米,明旦去之。虜夜聞量籌,曉見棄粟,謂降者欺己。”[112]元嘉中,檀道濟與北魏軍交戰,因糧食匱乏,命人夜間用沙冒充穀物,唱籌計量,以欺騙敵方。“量沙”場景當近於量榖,此“量籌”之籌,即後世所謂籌子。
以下幾例單枚的簡札,它們所記錄的糧食數額固定,因而有可能是籌,或有可能用為籌: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14】入粟大石廿五石 車一兩 居攝三年三月戊申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居延新簡E.P.T7:10,殘長10.2厘米,寬1.2厘米,木質)[113]
【15】出粟大石廿五石 車一兩 始建國二年正月壬辰訾家昌里齊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居延新簡E.P.T59:175,長22.5、寬1.2厘米,木質)[114]
【16】入粟大石廿五石 車一兩 正月癸卯甲渠官掾譚受訾家茂陵東進里趙君壯就人肩水里郅宗
(居延新簡E.P.T59:100,長22.5、寬1.1厘米,木質)[115]
【17】出粟二石 廩夷胡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居延漢簡177.10,長23.1、寬1.1厘米。木質)[116]
【18】出粟二石 廩候長楊禹六月食
(居延漢簡177.13,長19、寬1厘米,木質)[117]
【19】出粟二石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居延漢簡250.5,殘長3.7厘米,寬1.2厘米,木質)[118]
【14】的紀年為“居攝三年”(3年),用西漢孺子嬰年號。這是“入粟”的記錄。“粟大石廿五石”是當時一輛車的運載量。【15】的紀年為“始建國二年”(10年),用王莽年號。這是“出粟”的記錄,數額也是“大石廿五石,車一兩”。【16】無紀年,是“入粟”的記錄,數額同樣是“大石廿五石,車一兩”。【17】、【18】、【19】是“出粟”的記錄,無紀年,數額皆“二石”。
以上所舉十餘例,皆以“升斗斛(石)”系列爲計算單位。其中,西漢時期的例子,最大計算單位全部用“石”;新莽時期和東漢初的例子,最大計算單位既用“石”(“大石”和“小石”),又用“斛”;[119]三國和西晉時期的例子,最大計算單位全部用“斛”。
這些例子表明,在糧食出納的現場,出納記錄大都書寫在條狀的券或簡札上。其後,這些券和簡札會被集中起來,經過整理,編製成“穀出入簿”。漢簡中此類資料不少,但多已散亂。有些“穀出入簿”留下了標題,如“遠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有幾件簿冊完整地存留到今天。實物資料顯示,此類記錄賬目的簿冊的確是先書寫文字,然後用繩子編連的。編繩完整的懸泉漢簡之《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121]和居延新簡之《勞邊使者過界中費簿》(74.EJT21:2-10)[122]可以爲證: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
《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 《勞邊使者過界中費簿》
照片顯示,這兩件簿冊的編繩都壓蓋在墨跡之上(見《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的下編繩、《勞邊使者過界中費簿》的上編繩),墨跡本身並沒有因編繩經過而留下空白,可知是書寫在先,編連在後。前文所舉第【13】例有兩處擾亂墨跡的繩痕,可知原曾有編繩壓蓋在墨跡之上,亦是一證。此外,前文所舉【1】、【5】、【8】、【9】等例,其整枚券或簡札上都布滿文字,墨跡清晰,而這些墨跡上皆未見與編繩有關的空白。
對於《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這件記錄糧食出納的簿冊,還應進一步考察。今試作釋文:
(第1枚)出穬麥小石十六石 建昭三年四月辛亥,倉嗇夫竟付縣泉廄佐延年
(第2枚)出穬麥小石十六石 建昭三年四月癸丑,倉嗇夫竟付縣泉廐佐延年
(第3枚)出穬麥小石廿四石 建昭三年五月甲子,倉嗇夫竟付縣泉佐延年
(第4枚)出穬麥小石七石 建昭三年五月丙寅,倉嗇夫竟付縣泉廐佐延年
(第5枚)●凡穬麥小石六十三石
(第6枚)建昭三年六月丙戌朔丁未,淵泉守長長、守丞□移縣泉置:嗇夫□持傳馬□□使者諸國客,廩如牒。今寫券墨移,書到,□令史受,薄(簿)入七月。報,毋令繆,如律令。
“建昭”,西漢元帝年號;“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此簿冊由6枚木札組成,前4枚是四月、五月的4條“出穬麦”記錄,第5枚是對以上賬目的結算,第6枚是六月丁未淵泉縣發送給縣(懸)泉置的文書。該文書是在四、五兩月的“出穬麦”記錄結算之後,連同賬目一起發送的。查看4枚記錄“出穬麦”的木札,見其並無刻齒或墨書的同文標記,但其內容、格式與前面所舉的【1】、【2】兩例“出券”非常相像。[123]
“券墨”當作何解?有研究者以“今寫券墨移書”爲句,認爲“券墨移書,即用墨筆書寫的可作爲正式憑據的文書送交者”。[124]這種說法較爲含糊,似乎將“券墨移書”當作了批准支取糧食的憑據文書。然而通觀《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全文可知,當“今寫券墨移”時,支取糧食之事已經完成,故疑此說法不確或有誤。
又,《九章算術·方程》劉徽注:“今兩算得失相反,要令正負以名之。正算赤,負算黑,否則以邪正為異。”[125]沈括《夢溪筆談·象數二》亦曰:“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126]而《周書·蘇綽傳》卻記載:“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127]按此,算籌的“正赤負黑”似乎與計帳的“朱出墨入”相互矛盾。其實,“負與正”、“出與入”都是相對的。對於出納雙方,此方的“負”、“出”,就是彼方的“正”、“入”,反之亦同。而“券墨”與上述說法有否關聯?囿於材料短少,目前還難以判斷。
《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的主要內容是輸出糧食的賬目。上文已經提到,這些賬目的內容、格式與“出券”非常相像。六月丁未的文書說“今寫券墨移”,則“券墨”或與糧食出納的記錄有關。另有一條懸泉漢簡可以參看:
神爵二年正月丁未朔己酉,縣(懸)泉置嗇夫弘敢言之:遣佐長富將傳迎長羅侯,敦煌稟小石九石六斗,薄(簿)入十月。今敦煌音言不薄(簿)入,謹問佐長富稟小石九石六斗,今移券致敦煌□……。
(懸泉漢簡I 0309③:215)[128]
此應是懸泉置嗇夫寫給敦煌郡府的文書。由該文書可知:因“遣佐長富將傳迎長羅侯”而領糧小石九石六斗,懸泉置將此賬記入了十月的簿冊;而今敦煌方面說“不薄(簿)入”,故懸泉置要求詢問“佐長富”,並將“券”(或“券致”)移送敦煌。則此“券”(或“券致”[129])當與領糧的手續有關,並可作爲已經領糧的證據。將該文書的“今移券”(或“今移券致”)與《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的“今寫券墨移”對比,見二者頗似,這說明“券墨”的確可能牽涉糧食出納的記錄。
《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所謂“券墨”,應就是指賬目中的那4條“出穬麦”記錄。而那4條“出穬麦”記錄則應抄自券文,進一步說,應抄自分券所得的半券(此處為4枚“出券”的集合)之文。故疑“券墨”指券文或半券之文,“今寫券墨移”則為“今抄寫券文(或半券之文)並移送”之意。“出券”收存於出糧方,這裏的出糧方為“倉嗇夫竟”所在的糧倉,從六月丁未的文書看,該糧倉似當轄屬於淵泉縣。“出券”在匯總時被抄寫、編連、造簿,就形成了本簿冊《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淵泉縣再將本簿冊發送給入糧方,這裏的入糧方為“縣(懸)泉廐佐受年”所在的懸泉置,即4件“穬麦出入券”之“入券”的收存處。懸泉置接文後也要造簿,並給予回覆。這些糧食出納記錄被如此整理和周轉的目的,恐與核校計賬等事務有關。附帶說一下,《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中的4條“出穬麦”記錄,其文字內容、格式不僅與已知是券的例【1】、【2】相像,它們與例【8】、【9】也很相像,僅有“出”、“入”之別。則例【8】、【9】也有可能是券的抄文,即2件“出入券”之“入券”的抄文。以上所說,只是對“券墨”的試探。這一問題的真正解決,尚需更多的證據和進一步的研究。[130]
餘 論
上文所舉簡牘諸例及《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都有關官倉。有關漢晉時代的私倉的資料,尤其是有關私倉的糧食出納的資料,目前還所知很少。而在本文所討論的這幾幅倉廩圖裏,卻既有官倉,又有私倉。對於圖1,研究者多認爲是地主向農民收取私租的場景,[131]其糧倉則爲私倉。這一觀點似值得商榷。首先,本圖所屬密縣打虎亭一號漢墓的墓葬規格頗高,結構宏偉複雜,顯示出墓主人享有尊貴的地位。據考證,其身份很可能是弘農太守。[132]再查看圖中糧倉,見其爲方形,規制講究,是大型重簷倉樓,欄杆、曬臺、氣樓俱全,倉前場地開闊。再查看圖中諸人,見其多達十位,但甚少農民模樣的人物。除一形體極小的騎馬射鳥者及其隨從外,眾人都在忙於糧食出納事項,私家生活氣息淡薄。人物中較爲突出的,是手執簡牘的跪者和與之對面的坐者,而從他們的服裝、舉止看,這兩個人的關係不似農民與地主,卻頗似小吏與其長官。將這些情況綜合起來考慮,可知此糧倉未必是私倉,而有可能是官倉。本圖的含義,或與某些榜題爲“某某食此大倉”的墓葬倉廩圖相似,[133]是爲了表明墓主人享有“大倉”的供給。“大”通“太”,“大倉”即國家之“太倉”。[134]圖2係出自畫像磚。畫像磚的製作,是用雕刻好的木製印模將圖像壓印在磚坯之上,然後進行燒製而成,[135]其圖像的程式化傾向較爲突出。本圖中的糧倉,圖像簡單,人物亦少,官私特徵似乎不很分明。然而從倉前坐者的衣冠、運糧的馬車以及此類畫像磚所具有的共性來看,該糧倉很可能是官倉。圖3中的糧倉,因其牆壁上有墨書“護烏桓校尉莫(幕)府穀倉”,可確知是官倉。“護烏桓校尉”亦與該墓墓主人的仕宦經歷一致。[136]圖4中的糧倉所展示的是出糧景象,其場所大,儲糧裝置多,分券者貌似官吏,故疑為官倉,其含義或亦與榜題為“某某食此大倉”的墓葬倉廩圖相似;[137]圖5、圖6中的糧倉,因其整幅畫面頗具私家生活氣息,如圖5中有墓主人模樣的男子觀糧的畫面、[138]手握簡牘的畫面,圖6中有佔據突出位置的婦女和兒童的形象等,可推知是私倉。此二圖所屬的墓葬,亦皆顯示其墓主人不是官員,而是具有經濟實力的豪強地主。[139]
但要指出,對於倉廩圖中的糧倉規模,尤其是其官、私性質,不可過於拘泥或深求。在查看此類畫像資料的時候 ,有兩點應當注意 。其一 ,本文在開始時已提到,墓葬中的畫像一般具有誇飾的成份 ,倉廩圖亦不例外 。漢晉是農業社會 ,生產力水平尚低 ,食糧與人們的生計密切相關 。在當時 ,能夠擁有或享用倉廩是富足的標志 ,倉廩越大 ,越顯示豐裕 。故墓葬的隨葬品中常見陶倉 ,畫像中常見關於糧倉的題材。《急就篇》曰:“ 廩食縣官帶金銀。” 顏師古注:“廩食縣官,官給其食也。帶金銀者,或得封侯,或受職任,皆佩印也。” “縣官”,指國家或天子;“金銀”,指王侯和高官之印。[140]“廩食縣官”不僅代表富足,亦代表身份的尊貴。大約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在倉廩圖中刻畫官倉遂成風尚,其規制則往往追高摹大,未必與實情相符。“食此大(太)倉”之演變爲一種套語,[141]“太倉”之提升爲“天倉”,[142]亦可以爲證。
其二,在私倉(尤其是較大的私倉)與官倉之間,也確實可能有某些相通之處。當時,民間的經濟活動尚較簡單,其習俗、規則等或模仿公家。例如,《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前漢紀·文帝紀》載荀悅曰:“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143]董、荀所議論的都是小農向“豪民”繳納私租的情況。是地主的私租亦可稱作“稅”、“賦”,擬於官府。由此推想,當時私倉的管理方式亦很可能與官倉略似。圖5和圖6所展示的糧食出納場景,便是其例。
還要考慮到,墓葬畫像係出自當時從事該行業的畫工之手,畫像的定稿過程會受到多方面的影響。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以上所述喪家雇主的身份、意願和時代所決定外,不同地域的畫工往往會因襲、參用其所屬作坊團體內傳承的舊畫稿,也會加入其個人的認識、風格和創造。最終完成的畫像,很可能是綜合了各種因素的複雜的結果。因此,對於墓葬倉廩圖中的糧倉,須仔細辨識,審慎探討。
綜上所述,在漢晉時期,糧食出納的記錄通常都書寫在竹木製作的券或簡札上。在本文討論的這幾幅倉廩圖裏,當糧倉、量器與各色相關的人、物等被組合起來,一同出現的時候,我們不難認出這是糧食出納的場景。在該場景中,有人頗似糧倉的倉主、主管人或辦事者,其手中持物,我們可推測此或與糧食出納的手續相關。再進一步觀察,看到該物爲數支細棍或集成束狀,我們便知這很可能是簡牘,具體地說,很可能是書寫在券或簡札上的糧食出納記錄。它們被成把地刻繪在倉廩圖裏,應是爲了顯示倉廩的豐實與興旺。我們今日則可視之爲簡牘時代的遺痕。
附錄:其它有關資料
(略)
附記:本文初稿完成於2009年5月,發表於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12屆年會(2009年8月,河南永城)。修訂稿完成於2009年12月。本文寫作中,曾蒙邢義田先生賜教,謹致謝忱。
(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七集,商務印書館,2011年)
(編者按:[1]例如,對本文所引圖1,安金槐、王與剛的說明是:圖中一人作跪姿,“雙手捧物,似爲記賬之簡冊”;孫心一的說明是“雙手捧著簡冊”。安金槐、王與剛:《密縣打虎亭漢代畫像石墓和壁畫墓》,《文物》1972年第10期,第53頁;孫心一:《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縮影——東漢畫像石“豪強地主莊園的糧倉”簡介》,《史學月刊》1981年第5期,第85頁。
[2]例如,對本文所引圖2,《中國畫像磚全集》一書的說明是“倉前一人席地而坐,執籌計數”。《中國畫像磚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磚全集:四川畫像磚》,四川美術出版社2005年版,“圖版說明”第62頁。“執籌計數”這一說法較為含糊。籌可指作為算具的算籌,也可指代表一定數額的物、錢的籌子。從該書行文看,似是指算籌。又,對本文所引圖5,《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一書的說明是“一尊者坐於榻上,雙手持算籌”。鄭岩:《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頁。
[3]例如,對本文所引圖1中的跪者,《密縣打虎亭漢墓》一書稱其“雙手捧物”;《中國畫像石全集》一書則稱其“雙手執物”。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縣打虎亭漢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頁;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石全集》6《河南漢畫像石》,河南美術出版社、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圖版說明”第31頁。
[4]例如《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一書對本文所引圖5的說明。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6頁。
[5]例如《山東省博物館館藏精品》一書對本文所引圖4的說明、《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一書對本文所引圖6的說明。分見魯文生:《山東省博物館館藏精品》,山東友誼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頁;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第84—86頁。
[6]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石全集》6《河南漢畫像石》,“圖版說明”第31頁。原圖見第70頁。
[7]《中國畫像磚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磚全集:四川畫像磚》,第108頁,圖版一四五。
[8]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爾漢墓壁畫》,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頁,前室西壁壁畫。
[9]魯文生:《山東省博物館館藏精品》,第276——277頁。此圖係承邢義田先生示知。
[10]黨浩等:《山東長清大街村發現漢代畫像石墓》,《中國文物報》2006年1月18日第1版。
[11]《山東省博物館館藏精品》一書將此字誤釋為“升”,見第276頁。
[12]疑此物或為量糧時用來刮平榖粟的“槩”。《韩非子·外储说》:“槩者,平量者也。”或為量糧時發放的“籌”(詳後文)。
[13]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圖版二,M37西壁北側畫像磚。
[1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第84頁、86頁。
[15]《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一書認爲是“象徵性樓梯”。見該書第86頁。
[16]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第86頁。
[17]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第16頁。
[18]鄭岩指出:“在當時畫工的眼中,這些看似獨立於每塊磚上的畫面是統一設計、互相關聯的,並不像我們 在一幅幅印刷精美的圖版中看到的那樣彼此毫不相干。”鄭岩:《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第146頁。
[19]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圖版八,M39西壁南側畫像磚。
[2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第85頁、第86頁。
[21]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第25頁。
[22][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七上《釋宮》,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209頁。
[23][元]王禎撰、繆啟愉譯注:《東魯王氏農書譯注》,《農器圖譜集·倉廩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68頁。
[24]《毛詩正義》卷一九《周頌·豐年》,《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594頁。
[25][元]王禎撰、繆啟愉譯注:《東魯王氏農書譯注》,《農器圖譜集·倉廩門》,第669頁。
[26][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六《富國篇》,《諸子集成》二,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6頁。
[27]《漢書》卷二四《食貨志》,第1162頁。本文所引《漢書》,皆中華書局標點本。下同。
[28]《晉書》卷二六《食貨志》,中華書局標點本,第784頁。
[29]《史記》卷一○五《扁鵲倉公列傳》,第2808頁。本文所引《史記》,皆中華書局標點本。下同。
[30][清]戴望:《管子校正》卷二四《輕重丁》,《諸子集成》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12頁。
[31][漢]史游:《急就篇》,四部叢刊續編本。
[32]四川大學歷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甲骨金文字典》,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403頁。
[33][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卷五《釋宮室》,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頁。
[34][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卷五《釋宮室》,第283—284頁。
[35]《毛詩正義》卷一三《周頌·豐年》,《十三經注疏》,第467頁。
[36]《後漢書》卷三一《蘇章傳附不韋傳》,中華書局標點本,第1108頁。
[37][清]戴望:《管子校正》卷一八《度地篇》,《諸子集成》五,第305頁。
[38]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00頁。
[39]關於漢代糧倉的形制與分類,可參看靳祖訓:《中國古代糧食貯藏的設施與技術》,農業出版社1984年版,第32—70頁;杜葆仁:《我國糧倉的起源和發展》,《農業考古》1984 年第2期、1985年第1期;呼林貴:《古代倉名考》,《農業考古》1985年第1期;張鍇生:《漢代糧倉初探》,《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245頁;〔日〕秋山進午:《漢代の倉庫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第46期(1974年),第3-13頁等。
[40]規模較大的糧倉多有氣樓。對於這種建在糧倉頂部有檐、有窗的通氣結構,研究者往往稱之爲“氣窗”。而在文獻記載中,其正式名稱是“氣樓”。如[宋]洪邁《夷堅志·鄂州總領司蛇》:“鄂州總領司,故州治也……蛇往來東西,或入教塲大井内,或從府倉氣樓中垂頭下而食米。”(《夷堅志》夷堅支乙卷九,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863—864頁)[宋]龍衮《江南野史》:“躍囷簷,自氣樓間入竊官粟,數十往。”(傅璇琮等:《五代史書彙編》9,《江南野史》卷一○,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225頁)《欽定大清會典》卷七二《工部·營繕清吏司·城垣》:“凡倉厫之制……檐高丈五尺有竒,下藉青甎,上加木版,牆址留下孔,以洩其濕,厫頂建氣樓,以散其蒸。”(《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通制之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本,第619冊,第669頁)
[41]可參看本文附錄之圖1—19、圖29—33。
[42]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石全集》6《河南漢畫像石》,圖版說明第31頁。安金槐、王與剛則說“席上置斗(斛)”。安金槐、王與剛,前引文,第53頁。
[43]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第83頁、第84頁。該書對這幅倉廩圖的分割情況詳上文。
[44]可參看本文附錄之圖23—28中的量器。鄭岩指出:該男子“捧筒形器,疑為量”。但未說明是何種量器。鄭岩,前引書,第151—152頁。
[4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第84—85頁。
[46]《漢書》卷二一《律曆志》,第967頁。
[47]何寧:《淮南子集解》卷一七《説林訓》,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197頁。
[48][漢]劉向:《說苑》卷一八《辨物》,《漢魏叢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453頁。
[49][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三《辯證一》,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頁。
[50][元]王禎撰、繆啟愉譯注:《東魯王氏農書譯注》,《農器圖譜集·倉廩門》,第673頁。
[51][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八上《釋器》,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頁。按:“桶, 木方,受六斗”句,《說文·木部》“斗”原作“升”,當爲字形之訛。
[52]例如居延漢簡:“出穈小石三石,爲大石一石八斗,以食卒三人”(275.2);“入穈小石十二石,爲大石七石二斗”(273.9);“大石六石,爲小石十石”(275.22)。見謝桂華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本文所引居延漢簡之釋文,皆出此書。下同。
[53]《宋本廣韻》卷二《下平聲·蕭韻》,北京市中國書店1982年版,第124頁。
[54]或說“𣂀”同“庣”。《說文·斗部》桂馥義證:“𣂀,或作庣。”而《漢書·律曆志》曰: “十斗爲斛……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注引鄭氏曰:“庣,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氂五豪,然後成斛。”師古曰:“庣,不滿之處也。”又《廣韻·蕭韻》:“庣,不滿之皃。”按此,一個邊長一尺的正方形的外接圓,將其直徑(即該正方形的對角線)的兩端各延長九氂五豪,就是斛口的直徑。則“庣”可視爲斛口之圓與邊長1尺的正方形的外接圓的半徑差。是“𣂀”、“庣”不同。
[55]此器的形制,與《漢書·律暦志》所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相符。
[56]參看國家計量總局主編:《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84—98頁。關於新莽銅嘉量的資料,見劉復:《新嘉量之較量及推算》,《輔仁學志》1928年,1卷1期,第17—18頁。
[57]在明清時期,1石 = 2斛,1斛 = 5斗。明代 1斗 =10225毫升, 清代1斗= 10355毫升。參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頁《歷代量器容積對照表》。關於漢代小斛(石)的容積,研究者有兩種不同意見:一說爲12000毫升,一說爲20000毫升。筆者同意前者,並擬另文專考,茲不贅。
[58]《宋本廣韻》卷四《去聲·線韻》,北京市中國書店1982年版,第390頁。
[59]參裘錫圭:《漢簡零拾》,《文史》第12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4—35頁。
[6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本文所引居延新簡之釋文,皆出此書。下同。
[61]例如居延新簡:“尉史鮮于惲,七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E.P.T49:52)“第廿七長張德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卒池信食三石二斗二升少。卒忠食三石二斗二升少。卒暴便食三石二斗二升少。”(E.P.T51:247)“卒彭偃粟三石三斗三升少,自取。”(E.P.T52:562)
[62]見圖1—2。
[63]見圖2—2、圖5—2。算籌因其功用的不同,大致可分爲博具、算具兩類。前者通常以6枚爲度,長度大於後者。參張沛:《出土算籌考略》及所附《歷年出土算籌一覽表》,《文博》1996年第4期,第54—55頁。本文討論的是後者。
[64]《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381頁。
[65]《漢書》卷二一《律暦志》,第956頁。
[66]參張沛,前引文及附表,第55頁。據該表,1954年—1986年共出土了16批算籌,其中5批是博具類算籌,11批是算具類算籌。在算具類算籌中,長度爲14厘米以下的共8批,長度爲16、20厘米的各1批,另有1批長度不詳。
[67]李勝伍、郭書春:《石家莊東漢墓及其出土的算籌》,《考古》1982年第3期,第255頁。
[68]錢寶琮點校:《算經十書》,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542頁。《數術記遺》,舊題漢徐岳著、北周甄鸞注,錢寶琮認爲此書係甄鸞自撰自注,“反映了當時的某些數學思想”。
[69]《隋書》卷一六《律曆志》,中華書局標點本,第387頁。
[70]算籌長度之演變,參李勝伍、郭書春,前引文,第255頁;王青建:《試論出土算籌》,《中國科技史料》第14卷第3期(1993.3),第7頁。
[71]據張沛實驗,進行四五位數的四則運算,“至少要有現時辦公桌大小的地方才能進行”。張沛,前引文,第57—58頁。
[72]李儼:《中算家的記數法》,《數學通報》1958年6月號,第248頁。
[73]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頁。
[74]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31頁。
[75]寶雞市博物館、千陽縣文化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千陽縣西漢墓中出土算籌》,《考古》1976年第2期,第85頁、第108頁。算(筭)袋、算(筭)囊在文獻中的記載,見《舊唐書》卷五《髙宗紀下》:“一品已下文官並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 [宋]任廣:《書叙指南》卷四:“筭袋,曰筭幐。”[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九《釋魚》:“烏鰂狀如算囊,兩帶極長。海人云:秦王東遊,棄筭囊於海,化爲此魚。”
[76]李勝伍、郭書春,前引文,第255頁。
[77]參胡平生:《木簡出入取予券書制度考》,載《胡平生簡牘文物論集》,台北,蘭臺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頁、第102—103頁。
[7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掘報告》,岳麓書社2006年版,第211頁,彩版二十四.1。
[79]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頁釋文,第47頁圖版。
[80]據張春龍:《里耶秦簡祠先農、祠和祠隄校券》,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93頁。因里耶秦簡尚未全部公佈,無從識考,暫附記於此。
[81]此法施於“露布”的文告和傳信等。其泥封、抑印的目的與“檢”有別,不是爲了封閉、緘護文書,而是彰示發佈者並證以印信,性質与後世在紙文書上蓋印章相同。另,居延漢中有一些寫在單枚木牘上的負債文書,文中有“以印為信”之句,在木牘的中央(或接近中央的部位)留有空白,如居延新簡E.P.T51:225,E.P.T52:88,E.P.T52:544等。有學者認為,這是“在簡上直接加蓋封泥”之處(角谷常子::《木簡背書考略》,《簡帛研究譯叢》第一輯,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227—228頁)。查看此類木牘,在其留空的旁側往往有較長的缺口。當沒有封泥槽而又需要蓋印時,或可通過此缺口來捆綁和固定繩子,用繩子製成印窠,然後填泥抑印。又據《續漢書》志二五《百官二》記載,漢代宮門使用“鐵印文符”。注引胡廣曰:“符用木,長尺二寸,鐵印以符之。”(第3581—3582頁)木符上的鐵印,或係烙印。
[82]《漢書》卷六四《終軍傳》記載,漢代以“繻”爲出入關的憑證。注引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第2820頁)可知憑證亦有用帛來製作的。但帛較貴,不如簡牘使用廣泛。
[83]可分爲三份的券稱爲“參辨券”。《睡虎地秦墓竹簡·金布律》曰:“縣、都官坐效、計以負賞者,已論,嗇夫即以其直錢分負其官長及冗吏,而人與參辨券,以效少內。”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61頁。又《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金布律》曰:“官爲作務、市及受租、質錢,皆爲,封以令、丞印而入,與參辨券之,輒入錢中,上中辨其廷。”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中国历史名人故事 励志故事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頁。[84]參于豪亮:《秦律叢考·券右 辨券》,《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2-133頁;馬怡:《里耶秦簡中幾組涉及校券的官文書》,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頁。
[85]《禮記正義》卷三《曲禮上》,《十三經注疏》,第1244頁。
[86]例如嘉禾吏民田家莂,其“形制特殊,長49.8—56厘米”。見《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冊),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頁。
[87]此木券的照片係承張俊民先生惠賜,謹此致謝。
[88]《周禮注疏》卷三《小宰》,《十三經注疏》,第654頁。
[89]關於券書刻齒的作用,參于豪亮,前引文,第132頁;山明:《刻齒簡牘初探——漢簡形態論引緒》,收入張傳璽:《契約史買地券研究》附錄,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335—339頁;邢義田:《一種前所未見的別券——讀<額濟納漢簡>札記之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2008.3.28。
[90]參胡平生、汪力工:《走馬樓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合同符號研究》,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247頁。
[91]胡平生、汪力工認爲:刻齒與“同”字這兩種契約標識“功用相似”,它們是不同源而同時並存,還是時代有早晚、由前者向後者演進發展的關係,目前尚無法斷定。胡平生、汪力工,前引文,第249頁。
[92][唐]徐堅等:《初學記》卷二一《文部·紙》,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17頁。
[93]王國維:《簡牘檢署考》,《雲窗叢刻》本。
[94]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一,1957年,第185、184頁。按:本文所記券和簡札的長度與寬度,皆係筆者據相關圖版測得,下同。
[95]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第185、184頁。
[96]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華書局1994年版,圖版第409頁。
[97]長沙簡牘博物館等:《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上冊第41頁圖版,下冊第724頁釋文。
[98]長沙簡牘博物館等:《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上冊第78頁圖版,下冊第732頁釋文。
[99]侯燦、楊代欣:《樓蘭簡紙文書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13頁。按:釋文中的墨書標記“”,原誤作“”,今據圖版改。從出入券書之規則看,“出券”亦應是右券。
[100]侯燦、楊代欣:《樓蘭簡紙文書集成》,第434頁。
[101]參山明,前引文,第329頁。
[102]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第38
讲好身边的中国历史故事
9頁。[103]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第440頁。
[10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圖版第444頁。
[10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圖版第62頁。
[106]長沙簡牘博物館等:《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上冊第18頁圖版,下冊第719頁釋文。
[107]長沙簡牘博物館等:《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上冊第347頁圖版,下冊第795頁釋文。
[108]承參與走馬樓吳簡整理工作的羅新先生告知:在走馬樓吳簡中,與例【13】類似的竹簡數量很多,皆先寫後編;在這些竹簡的上半段和下半段各有一處爲編繩預留的空白,用墨畫出兩三條橫線;今編繩已朽滅,該處僅存繩痕和擾亂的墨痕。
[109][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繫傳》通釋九,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第89頁。
[110][漢]史游:《急就篇》,四部叢刊續編本。
[111]例如《史記》卷三〇《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第1430頁)又江陵鳳凰山10號漢墓簡牘:“市陽二月百一十二算,算八錢,八百九十六,正偃付西鄉偃佐纏,傳送。卩。市陽三月百九算,算九錢,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鄉偃佐賜。市陽三月百九算,算廿六錢,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鄉偃佐賜。”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頁,806號。
[112][唐] 許嵩:《建康實録》巻12《宋太祖文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6頁,元嘉八年二月條。又《南史》卷一五《檀道濟傳》:“道濟夜唱籌量沙。”(第446頁)
[113]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圖版第39頁。
[11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圖版第361頁。
[11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圖版第354頁。
[116]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第91頁。
[117]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第83頁。
[118]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第559頁。
[119]有研究者指出,西漢簡牘皆以“石”爲容量詞,新莽始建國至天鳳年間、東漢初則“石”“斛”並用。見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12 頁。
[120]吳礽驤等:《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頁。
[121]《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的照片,見張俊民:《〈額濟納漢簡〉冊書質疑》附圖四,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文庫·漢簡專欄》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4,2006年4月12日。
[122]《勞邊使者過界中費簿》的照片,見馬建華主編:《河西簡牘》,重慶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
[123]但例【2】尚未剖分。詳上文。
[124]見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八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頁註釋。
[125]郭書春匯校:《九章算術》卷八《方程》,遼寧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88頁。
[126][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八《象數二》,第49頁。
[127]《周書》卷二三《蘇綽傳》,中華書局標點本,第382頁 。
[128]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二一二,第147頁。
[129]致,送至,亦指領取東西所用的文書。《睡虎地秦簡·田律》:“稟大田而毋(無)恒籍者,以其致到日稟之,勿深致。”整理小組註:“致,《曲禮》:‘獻田宅者操書致。’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按猶券也。’”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9頁。並參裘錫圭:《漢簡零拾》,《文史》第12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3頁。
[130]今見漢簡所記“券墨”,皆與會計之“出入賬”有關。例如,居延新簡:“庚辰朔戊申,第十桼候長良敢言之:謹移卒輸官財用券墨如牒。敢言之。 連局令校。”(E.P.T2:9A)又懸泉漢簡:“永光三年正月丁亥朔丁未,淵泉丞光移縣(懸)泉置:遣廄佐
中国历史对联小故事
賀持傳車馬迎使者董君、趙君、所將客,柱(住)淵泉,留稟茭。今寫券墨移,書受,薄(簿)入二月。報,毋令謬,如律令。”“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魚離置嗇夫禹移縣(懸)泉置:遣佐光持傳馬十匹,為馮夫人柱(住),廩穬麥小卅二石七斗,又茭廿五石二鈞。今寫券墨移,書到受,薄(簿)入三月。報,毋令繆(謬),如律令。”“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淵泉丞賀移廣至、魚離、縣(懸)泉、遮要、龍勒:廄嗇夫昌持傳馬送公主以下過,稟穬麥各如牒。今寫券墨移,書到受,薄(簿)入十一月。報,毋令繆(謬),如律律令。”(《敦煌懸泉漢簡釋粹》85,I 0111②:3;203,II 0115③:96;205,II 0114③:522)當時的出入帳目,應以券為依據。[131]例如,《密縣打虎亭漢墓》一書認爲“這幅畫像真實地再現了漢代地主向農民收租的實景”;《中國畫像石全集》一書認爲其“真實地再現了漢代地主向農民收租之情形”;安金槐、王與剛、孫心一認爲該圖“刻畫了漢代地主盤剝農民的罪惡形象”,其中跪者是佃農,坐者是收租的地主;李錦山認爲是“大地主收租圖”;劉興林認爲是“大型收租圖”。分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前引書,第104頁;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石全集》6《河南漢畫像石》,“圖版說明”第31頁;安金槐、王與剛,前引文,第53頁;孫心一,前引文,第85頁;李錦山:《略論漢代地主莊園經濟》,《農業考古》1991年第3期,第115頁;劉興林:《漢代農業考古的發現和研究》,《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第14頁。
[132]《密縣打虎亭漢墓》一書指出,酈道元《水經注》洧水條所載弘農太守張伯雅墓的地理位置及其封土的情況,與密縣打虎亭一號漢墓可相互吻合。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前引書,第355—357頁;亦見安金槐、王與剛,前引文,第54—55頁。
[133]墓葬倉廩圖中的“食大(太)倉”類榜題,原意是爲了標榜墓主人及隨從係由國家“太倉”供應糧餉,祿食不盡。如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的榜題“上郡屬國都尉西河長史吏兵馬皆食太倉”、“繁陽吏人馬皆食太倉”,河北望山一號漢墓壁畫的榜題“□□□下□□皆食太倉”等。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爾漢墓壁畫》,第14頁;姚鑒:《河北望都縣漢墓的墓室結構和壁畫》,《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12期,第56頁。並參陳直:《望都漢墓壁畫題字通釋》,《考古》1962年第3期,第162頁。“食大(太)倉”後演變爲一種套語。
[134]沂南漢墓畫像石中的倉廩圖(見本文附錄之圖8)的情況與之類似,而該圖亦同樣被稱作“收租圖”。見山東沂南漢墓博物館編:《山東沂南漢墓畫像石》,齊魯書社2001年版,圖35(中室南壁橫額東段畫像局部),第79頁圖版說明。該圖并曾以“豪強地主田莊的糧倉”爲題被編入中學課本《中國歷史》(第一冊)。見孫心一,前引文,第84頁。
[135]參袁曙光:《四川畫像磚概論》,《中國畫像磚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磚全集:四川畫像磚》,第13頁。
[136]參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爾漢墓壁畫》,第10頁。
[137]關於本畫像石所屬墓葬的性質、墓主人的身份等情況,因目前未見發掘報告,僅有簡短的報導,故未詳。見黨浩,前引文,《中國文物報》2006-1-18第1版。
[138]見前引M37號墓的橫剖視圖(局部)。
[139]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第5章《墓葬年代與有關問題》,第106頁。
[140]《史記》卷五七《絳侯周勃世家》:“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縣官謂天子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第2079頁) 《後漢書》卷四七《班超傳》李賢注:“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第1583頁)
[141]在畫像中的例子,如四川邛崍出土的“糧倉畫像磚”,該圖像程式化明顯,其榜題則僅作“皆食此大(太)倉”五字;見劉振宇:《成都怡漢軒秘藏漢畫像磚精選》圖3“糧倉畫像磚”,《中國漢畫研究》第1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圖版第2頁及本文附錄之圖1。在碑刻中的例子,如《薌他君石祠堂題記》“此上人馬,皆食大倉”;《安國祠堂題記》“此中人馬,皆食大倉,飲其江海”;《曲阜徐家村畫像石題記》“此臧中車馬延□,龍虵虎牛皆食大倉”;《南武陽功曹闕題銘》“此上□□皆食□倉”等;見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日本京都,同朋舍1994年版,第118頁,第128頁,第134頁,第30頁。在此類套語中,“大(太)倉”已不必確指。
[142]例如山東蒼山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畫像石題記:“其當飲食就夫(天)倉,飲江海。”山東省博物館、蒼山縣文化館:《山東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墓》,《考古》1975年第2期,第126頁題記拓本;方鵬鈞、張勛燎:《山東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題記的時代和有關問題的討論》,《考古》1985年第3期,第276頁。又例如本文附錄之圖18。
[143]《漢書》卷二四《食貨志》,第1137頁;《兩漢紀·漢紀》卷八《文帝紀》,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14頁。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725.html
以上是关于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博物-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7241.html。
猜你喜欢
- 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里为什么一棵树都不栽种? 2023-08-14
- 清朝-清朝时期的宫女住在哪里? 2023-08-14
- 清朝-清朝12位皇帝的牌位还供奉在奉先殿吗? 2023-08-14
- 清朝-清朝时期谁有资格在故宫内骑马乘轿? 2023-08-14
- 秦始皇-揭秘:秦始皇因为一句什么谎言而修筑万里长城? 2023-10-22
- 火锅-揭秘:商周“鼎”或为最早火锅 汉代人已吃“鸳鸯火锅” 2023-10-22
- 秦始皇-揭秘:盗墓贼盗走秦始皇陵千年珍宝 却发生离奇一幕 2023-10-22
- 香妃-中国三大不腐女尸之一 惊天美貌疑是乾隆老婆香妃 2023-10-20
- 考古-宋朝女子的内衣是什么样的?又是怎样穿着的 2023-10-20
- 秦始皇-古今第一墓:为何秦始皇陵可以保存至今 2023-10-19


















